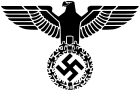赫尔曼·戈林
| 帝国元帅 赫尔曼·威廉·戈林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 |
|---|---|
 1943年的赫尔曼·戈林 | |
| 德国国会议长 | |
| 任期 1932年8月30日—1945年4月24日 | |
| 国家元首 | |
| 总理 | |
| 前任 | 保罗·勒伯 |
| 继任 | 无(职位废除) |
| 普鲁士帝国专员 | |
| 任期 1935年—1945年 | |
| 总理 | 赫尔曼·戈林 |
| 前任 | 阿道夫·希特勒 |
| 继任 | 普鲁士废除 |
| 德国经济部长 | |
| 任期 1937年4月—1945年4月 | |
| 总理 | 阿道夫·希特勒 |
| 前任 | 亚尔马·沙赫特 |
| 继任 | 瓦尔特·冯克 |
| 德国国家航空部长 | |
| 任期 1933年3月13日—1945年4月24日 | |
| 国家元首 | |
| 总理 | 阿道夫·希特勒 |
| 前任 | 无 |
| 继任 | 罗伯特·冯·格莱姆 |
| 德国林业部长 | |
| 任期 1934年7月—1945年4月 | |
| 国家元首 | |
| 总理 | 阿道夫·希特勒 |
| 前任 | 无 |
| 继任 | 无 |
| 个人资料 | |
| 别名 | |
| 出生 | 1893年1月12日[1] |
| 逝世 | 1946年10月15日(53岁)[2]× |
| 政党 | |
| 配偶 | |
| 儿女 | 埃达·戈林 |
| 专业 | 军人、政治家 |
| 内阁 | 希特勒内阁 |
| 宗教信仰 | 信义宗 |
| 获奖 | 列表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
| 服役 | |
| 服役时间 |
|
| 军衔 | 列表
|
| 指挥 | 德国空军(1935年–1945年) |
| 参战 | |
赫尔曼·威廉·戈林(德语: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关系极为亲密,在纳粹党内影响巨大。他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
戈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有着击落22架敌机的纪录,并获得德国最高级别军事勋章“功勋勋章”,战争后期还担任曾为“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所领导的第1战斗机联队最后一任指挥官。战后戈林加入纳粹党,为该党最早的一批成员,并参与了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期间身中枪伤。为此,后来他一直靠注射吗啡来减缓痛楚,结果终生毒品成瘾,体型也从健壮转为肥胖。1933年,戈林创立秘密警察机关“盖世太保”。1934年,他还颁布了纳粹统治下闻名的狩猎法案,该法保护了野生动物的繁衍与栖息,并大规模地进行都市绿化。1935年,戈林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并凭借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为空军取得大量预算与独立地位,令其快速建军。
戈林以德国空军最高领袖的身份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他本人并不直接干预作战细节,对现代化空军技术也缺乏了解,但还是对德军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敦克尔克战役、不列颠战役及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三场决定性战斗的发展;德国海军航空兵、空降部队和空军地面部队的建立、指挥反盟军轰炸作战等等。1940年德国打败法国后,戈林的权力与声望达到巅峰:希特勒将其晋升为“纳粹德国帝国元帅,高过传统意义上的德国元帅,隔年还指名戈林为其接班人。1942年后,随着德国军事情势恶化,戈林的声望和希特勒对其的信任逐渐降低,于是戈林从此不管政治与战争事务,专注于掠夺各占领地的艺术品与财物,奢华度日。
1945年4月22日,戈林得知希特勒将自杀,遂发电报告知希特勒,自己将接掌德国大权。希特勒认为此为逼宫的表现,便下令逮捕戈林,同时罢黜全部官职并开除党籍。德国二战投降后,戈林向美军投降,审判纳粹领袖的纽伦堡审判中还因为其精明的辩驳一度陷入胶着,但最终被判犯下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处以绞刑,但在行刑前一天晚上,戈林服毒自杀身亡。
家族背景
[编辑]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Marienbad)中出生[6],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母亲为海因里希的第二任妻子弗兰齐斯卡·蒂芬布伦(Franziska Tiefenbrunn)[7]。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现在的那米比亚)担任行政长官,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
弗兰齐斯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埃彭施泰恩医师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8][1]。海因里希与弗兰齐斯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8][1],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Karl Ernst)[注 1]、两位姐姐奥尔加(Olga)、葆拉(Paula)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注 2]。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丽亚·德内雷(Caroline Maria de Neree)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1][10]。
埃彭施泰恩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名“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11]。埃彭施泰恩是出身于柏林贵族、地主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12]。埃彭施泰恩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埃彭施泰恩算是半个犹太人。埃彭施泰恩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1][10]。戈林的母亲弗兰齐斯卡是埃彭施泰恩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偷情,这段关系约自亚伯特出生前九个月至一年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亚伯特实际上是埃彭施泰恩的私生子[13][14]。弗兰齐斯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不久后,弗兰齐斯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1896年,海因里希与弗兰齐斯卡皆已返回德国。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普鲁士柏林的弗里德瑙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但子嗣众多的他不怎么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严谨[1][15]。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16]。
早年
[编辑]
埃彭施泰恩拥有两座城堡,分别为位于萨尔茨堡郊外的毛特恩多夫和纽伦堡北部诺伊豪斯的费尔登施泰恩堡,埃彭施泰恩提供了后者供仅靠海因里希养老金维生的戈林一家生活[10]。埃彭施泰恩本人憧憬著中世纪贵族的奢华生活,故将城堡装饰的非常豪华,侍从人员也被要求穿着宫廷风格的服装工作,埃彭施泰恩也以城堡统治者的态度来接触城中的人们。一般认为,日后戈林对于奢华饰品的嗜好即是在这时期受教父的影响而来的[10][13]。相较之下,戈林的父亲辞去外交官职务后,每天过着饮酒度日的生活,使得在年幼的戈林眼中,父亲不再是个可依靠的人物,因此对于教父埃彭施泰恩的尊敬多于生父[17]。埃彭施泰恩对于戈林一家的孩子们也十分疼爱,一般认为尤其偏爱自己的儿子亚伯特,不过后者懦弱内向的气质与其不同,传记作者莫斯利认为之后埃彭施泰恩转而最为疼爱善于社交、具有冒险精神的戈林[13]。埃彭施泰恩常与弗兰齐斯卡共度夜晚,作为寄居者的海因里希即便有所不满也予以默认了。埃彭施泰恩的城堡内就这样维持着戈林父母和埃彭施泰恩这样奇妙的三角关系[12][18],一直到1913年因为埃彭施泰恩与一位年轻的女人——莉莉再婚,在后者要求下戈林全家搬离了法丁斯坦堡,前往憧憬已久的慕尼黑生活[11][19]。
戈林自10岁起就对登山运动极为热衷,在13岁时就登上了标高3,600米的大格洛克纳山山顶[20]。戈林还受到埃彭施泰恩的影响,培养了狩猎的兴趣[21]。1904年,戈林自菲尔特的小学毕业,随即送到了安斯巴赫的住宿制文科中学,但这对于过惯了城堡奢侈生活的戈林来说很不能适应。曾有一次班上上作文课,题目为“我最钦佩的人”,戈林写了他的犹太教父,却被校长约谈,要他写悔过书、再也不准写赞美犹太人的文章,同学也欺侮著戈林,在他脖子上挂了“我教父是犹太人”的牌子,并要他罚青蛙跳,戈林对此极为愤恨[22]。1905年一晚,他即打包行李逃离了学校,返回法丁斯坦堡[23]。
之后戈林在曾为骑兵军官的父亲与教父的推动下,于1905年进入巴登卡尔斯鲁厄的士官学校就读,并在1909年毕业,其中尤以骑术、历史、英文、法文等科目特别优秀[24]。1909年,戈林进入了柏林的大利希特费尔德的名校“普鲁士军官军校”就读[15][20]。1911年以“优等”成绩通过了下级上士(Fähnrich)的候补生考试,成为下级上士候补军官。1913年,戈林也通过了该校的高考(Abitur)[15]。身为名门军校优秀候补军官的戈林开始有了接触社交界的机会,累积了与上流阶级交流的经验[25]。1913年12月,戈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去世,尽管戈林在年少时不怎么尊敬父亲,但在慕尼黑的葬礼会场上仍旧痛哭失声[11]。1914年1月,戈林获陆军少尉军阶,被派至驻阿尔萨斯-洛林米卢斯的第112“威廉亲王”步兵团(Prinz Wilhelm,或称“巴登大公国步兵团)服役[15]。
第一次世界大战
[编辑]从陆军到跻身“王牌飞行员”
[编辑]
1914年7月末至8月初,欧洲各国间爆发了战争,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亦于1914年8月3日开战[26]。戈林所属的第112步兵团因为驻于法国国境一带,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开往战区。戈林带领的部队于米卢斯的攻防战中对法军的据点攻击,俘虏了四名法军士兵,因此战功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戈林不久后即罹患了风湿热,退下战场送往弗赖堡的医院休养[19][27]。
戈林住院期间,第112步兵团的朋友布鲁诺·勒尔策说服戈林自陆军步兵转至航空队[27],后者并开始于弗赖堡进行飞行训练[28]。戈林当时对于成为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但交付了调遣的志愿书后,许可令一直没有颁布下来。然而戈林违反命令,没有回去原本的单位服役,径自以勒尔策的信天翁式观测机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尔后此事被军方发现,戈林受到军法审判,判处拘留于兵营21天。但透过对宫廷有影响力的教父的帮助,在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出面下,戈林不仅免除了此罚,还顺利被调进航空队单位[19][29]。
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于第5集团军下的第25野战航空营(Feldflieger Abteilung 25,FFA25),为勒尔策驾驶的侦察机的观测员[30]。1915年春天起,勒尔策与戈林的飞机开始进入战场执行侦查任务,这种行动必须由勒尔策先飞到目标地后戈林要打信号告知其降低飞行高度,接着要自驾驶舱中以脚部支撑身体来架起摄影机拍摄,拍摄期间的数分钟还要忍受来自于地面的炮火攻击。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戈林相当擅长此类任务,成为一名拍摄多张高清晰照片的优秀观测员,不久后被取了个“飞天秋千”的绰号[4]。罗泽尔与戈林搭档在多架飞机失败后,成功拍摄了凡尔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因为此功绩,1915年3月罗泽尔与戈林两人一同被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31][32],也因为要说明照片之故,两人常被邀请出席高级军事会议[31]。
然而戈林并不满足于只做为观测员,1915年7月至9月继续于弗赖堡进行飞行员的进修课程,1915年9月戈林终于成为第25野战飞行营所属的战斗机飞行员。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出战,1915年11月,戈林与英军亨德里·佩奇制造的重型轰炸机遭遇,前者立即发动攻击,但英军索普威思战斗机击中了戈林,飞机因受损而难以操纵,戈林好不容易将飞机拉回至德方区,捡回了一条命,之后为了疗伤而脱离了战场约一年之久[33][31]。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战地[34],相继于第7战斗机中队、第5战斗机中队和第10航空补充营(Flieger Ersatz Abteilung 10)服役,击落敌机数也稳定地成长著。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为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3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中战斗开始白热化。戈林与罗泽尔两人的中队常并肩作战,于法兰德斯上的激烈空战里,曾有过戈林被法军飞行员瞄准而被罗泽尔所搭救,之后后者也被英军瞄准时,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发生[35]。
论及战技与斗志,戈林两方面皆受人认可,成为德军飞行员中最优秀的人物之一,还获得了“铁人赫尔曼”的别名[36]。与容易被忽略的陆海两军相比,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更受到瞩目,成为全德军的明星。他们的照片在德国上市,1917年后,戈林的照片开始出现于市场[31]。1917年10月,戈林获颁霍亨索伦皇家佩宝剑骑士勋章以及巴登大公国的卡尔·腓特烈骑士十字军功勋章[37]。接着1918年6月2日,德皇威廉二世为奖励戈林击落18架敌机的功勋,亲自颁发普通军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功勋勋章给戈林[37]。一般来说蓝色马克斯是颁发给至少击落25架飞机的飞行员,但当时戈林被视为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故作为特例,受勋事宜很快就被予以承认[38]。
“里希特霍芬联队”指挥官
[编辑]1918年7月7日,戈林被任命为素有“里希特霍芬联队”之称的第1战斗机联队的队长,此联队第一任队长为外号“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拥有80架击落敌机的战绩,为协约军敬畏的一位传奇人物,但该人于1918年4月21日阵亡。继任者威廉·赖因哈德也于7月3日在阿德勒斯霍夫的第二届“战斗机竞技会”(新型飞机的公开比赛)中试飞D.I战斗机时因机体空中分解而坠落身亡。下一任的队长职务一般被认为将由击落数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恩斯特·乌德特(62架)与埃里希·勒文哈特(54架)继任,但出乎众人意料地是由戈林被任命担任队长[39]。
里希特霍芬联队成员有乌德特、勒文哈特、洛塔尔·冯·里希特霍芬等诸多王牌,众人起初对戈林担任队长职务并不怎么认同。不过戈林发挥了自身的领导能力,他注重与其他王牌一同合作击落敌机,而非追求个人的累计战绩。至1918年8月初,戈林已获得了全联队的信赖,有着与第一任队长里希特霍芬相当的人望[40]。然而随着战局恶化,戈林联队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着补给和燃油不足的困境,而协约军的力量却逐渐增强。1918年9月,戈林的副官卡尔-海因里希·博登沙茨在日记中写道:“(局势的)紧张也在戈林中尉的脸上表露无遗,他的容貌转为消瘦和严峻,我们全体人员亦然。[41]”戈林指挥部队要战到最后,然而11月初,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叛变,最终蔓延到全国动乱,是为德国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逃到了荷兰。11月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共和政府于巴黎的贡比涅森林和协约军签署了停战协定[42]。随后,里希特霍芬联队收到命令,要求联队飞往斯特拉斯堡向当地的法军投降,但戈林与队员商讨后决定无视该命令,反飞向达姆施塔特。然而由于天气恶劣,联队部分成员被迫于曼海姆降落,被当地的工农委员会士兵夺取了武器,联队队员只得乘卡车去向戈林报告。戈林愤怒地率领联队其余飞机一同对工农士兵攻击,还迫使其写下道歉文[43][44]。之后,里希特霍芬联队飞到达姆施塔特时,故意将飞机着陆失败,把各机摔成一堆废铁,作为对协约军的最后的反抗行动[43][45][46]。战争结束,戈林的战斗机生涯共击坠了22架敌机[36],并终其一生都未曾遗忘战友,1943年时,其中一个前犹太队员被盖世太保所拘捕,戈林随即施压将该人救出、置于个人保护下[47]。
战间期活动
[编辑]流浪生涯
[编辑]
1918年12月,戈林返回慕尼黑与母亲居住,一路还与乌德特一家同行。戈林母亲的生活变得很困穷,教父人也在奥地利无法联络。当乌德特和戈林正为生活费发愁时,英国空军上尉弗兰克·博蒙特(Frank Beaumont)向戈林提供了资金援助。博蒙特曾于一战时为空军飞行员,被德军击落后成为俘虏,而戈林在当时曾保护过他[48][49]。
自从德国革命以来,慕尼黑受到以库尔特·艾斯纳为中心的多数派(即社会民主党)和独立派(即独立社会民主党)两大派系的社会主义政权所控制,而戈林参加了反对艾斯纳的政治团体。艾斯纳不久后被右翼青年军官暗杀,当地共产党人即发动革命,径自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并开始逮捕右翼和保守人士,戈林也是被追捕的目标。他借由博蒙特的帮助逃离了慕尼黑,投靠到听从柏林中央政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社民党政权)命令的“自由集团军”的保护伞之下。不久,“自由集团军”进攻慕尼黑摧毁了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并在慕尼黑市内屠杀共产党人,而戈林眼见左右两派彼此屠戮,对于德国的未来感到绝望[50][51]。
在这之后,荷兰航空公司福克寄给了戈林邀请,委托他前往丹麦哥本哈根为福克F.VII进行飞行展示。戈林决定接受此委托,将生活圈移到丹麦。他的特技飞行表演大获好评,福克公司也因此愿意出借飞机给戈林[52]。戈林也将表演生涯拓展到瑞典,一次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也使戈林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还常拉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旧队员一起来表演,此一事业为戈林赚进了大量的财富。博登沙茨后来回忆道:“这时的戈林过着就像一位冠军拳王的生活,有着大量的财富和美人作伴……戈林还曾在信中提到他在倒满香槟的浴缸里度过了一夜。[52]”
戈林在这段时期里与瑞典贵族之女、同时也是瑞典军人尼尔斯·冯·坎措男爵的妻子——卡琳·冯·坎措(旧姓福克(Fock))坠入情网,并于尼尔斯不在时将其夺走。1922年12月13日,尼尔斯与卡琳离婚[53];1923年2月3日,戈林带卡琳返回慕尼黑结婚[54][55][56]。
加入纳粹党到啤酒馆政变
[编辑]| 主题条目 |
| 纳粹主义 |
|---|
 |
1921年夏,戈林回到了德国,并于1922年至1923年期间就读慕尼黑大学,专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受到国家主义者的教授影响后,戈林倒向了国粹主义。1922年11月,戈林在慕尼黑国王广场的一次政治集会中与后来的纳粹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见了面,希特勒对初次见面的戈林热情地发表政治观:“必须撕毁《凡尔赛条约》”、“战争失败是因为受到犹太人和共产党在背后捅一刀的结果”……等等,戈林深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而后者也将这位曾获功勋勋章的空中战士视作可以利用的人才[57]。1922年12月,戈林加入了纳粹党(此时他的党编号不详,在1928年时则为23号)。1923年3月1日,尽管戈林加入纳粹党还不满一年,他被任命为冲锋队总指挥[15]。戈林在短时间内为冲锋队量身打造了军事化训练课程,大大改善这支团体的素质,遽闻当冲锋队在路上行军时已有路人会向其鼓掌送行[58]。希特勒对戈林颇为赞赏,他说道:“我交给他的是一群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把他们打造成一支为数11,000人的师。[59]”不过,戈林对于纳粹党本身的活动并不怎么在乎,他崇拜的是希特勒个人,同时戈林明显表现出轻视其他党内“同志”的态度,如鲁道夫·赫斯(后来的德国副元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种族理论者)等人[60]。
1923年8月末,戈林之母弗兰齐斯卡于慕尼黑逝世,后同父亲亨利葬于维斯特夫烈德霍夫墓园[61]。1923年9月2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成为了巴伐利亚邦总理[62]。卡尔不听从柏林中央的命令,还企图将巴伐利亚州独立,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好机会,他可以仿效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地方推翻中央的模式,让巴伐利亚的领袖们(主要由“三巨头”——邦总理卡尔、邦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邦警察总长汉斯·冯·赛瑟尔)与他合作,推翻柏林中央政府,因此对巴伐利亚政府加以煽动。然而柏林已严正警告,巴伐利亚若继续反叛将会受到军事镇压。因此,卡尔和他的政军领袖同志畏惧收手了。希特勒因此决定以武力强迫卡尔与巴伐利亚政府站在他这边,策划了政变行动[63]。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带着戈林与其率领的冲锋队闯入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当时卡尔正在那里发表施政演说。希特勒以手枪胁迫三巨头同他到酒馆的一处房间谈判,整个大厅则由全副武装的冲锋队所占领,群众开始鼓噪,戈林便大声说道:“没有什么要害怕的,我们没有恶意。喝你们的啤酒吧![64]”然而,房内的三巨头即使被手枪威胁也不愿与希特勒合作,后者见状便径自宣布新政府已经成立,对群众谎称总理等人已同意合作,众人立即的反应是喝采和欢呼,这稍微打动了仍被限制行动的三巨头。希特勒认为情势已在掌控之下,便将现场交给与纳粹党合作的前一战陆军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自己则驾车去处理其他琐事。洛索利用希特勒不在的机会,骗鲁登道夫说要去处理一些军务而离开,卡尔和赛瑟尔也跟着逃离了现场,不久,卡尔宣布希特勒的“合作”之说纯属假话,并下令将其逮捕。
当希特勒返回酒馆后发现巴伐利亚政府的要人已逃走,情势已经转坏,于是他与鲁登道夫商讨,决定利用后者在一战中的著名声望,领导纳粹党与其支持者向市中心进发,德国警察与军队应不敢对鲁登道夫开枪,甚至还可能加入他们。11月9日早,希特勒、鲁登道夫、冲锋队队长戈林与约3000名的队员开始向市中心的音乐厅广场前进,途中曾遭遇到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后者把守着一座桥梁不让希特勒等人通过,而戈林即前去威胁警察队长,若他对冲锋队开枪,他就要将押在队伍后端的人质枪毙,警察队长即不再阻拦他们[65]。可是当希特勒等人来到了音乐广场附近的“统帅堂”凉廊时,又有一支警队出现。这次鲁登道夫的名声不再有效,爆发了枪战。戈林在枪战中枪倒地,其中一颗子弹还贯穿了他的鼠蹊部,离动脉仅有几毫米的距离。冲锋队队员将他抬上车逃离现场,之后戈林受到一位犹太家具商之妻——伊尔莎·巴林(Ilse Ballin)的保护。由于巴林曾为护士,她也给戈林的伤势做了应急处理,并将他送到有亲纳粹医生的医院[注 3],戈林之妻卡琳得到消息后也前去该地。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戈林一家先是躲到加尔米施-帕滕基兴的卡琳朋友家中,后再逃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60][67][68]。
恢复政治活动
[编辑]
戈林在因斯布鲁克静养,受到奥地利纳粹支持者的欢迎,不但拍了许多电报慰问,还发起了相关的募款活动[69]。然而戈林的伤势严重,子弹深深地嵌进了他的体内,需要在右腿和腰部右侧开刀,这时医院用了吗啡作为麻醉药,使得戈林在伤势痊愈后对吗啡产生依赖,后成为彻底的吗啡中毒者[60]。
另一方面,德国这时已将政变的主要领导人纷纷拘捕。希特勒已被关入牢狱中,而巴伐利亚政府也正准备对躲在奥地利的戈林进行引渡程序,同时他在德国的财产也被冻结。此外,提早被释放的纳粹党政要恩斯特·罗姆也开始活动,开始建立新的冲锋队组织,冲锋队的实权已逐渐落入罗姆手中。戈林透过妻子向正被关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希特勒联系,后者命令戈林前往意大利、请求总理墨索里尼给予纳粹党金钱上的援助。为了保持自己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手边缺乏资金的戈林夫妇还是于1924年5月飞往意大利,但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和墨索里尼会面[注 4][70][71][72]。失望又灰心的戈林跟着妻子回到了在瑞典的娘家。由于原有的伤口持续阵痛,戈林几乎每天都注射吗啡,大量服药的结果使身体荷尔蒙分泌异常,导致原本英俊健壮的戈林身体走向肥胖[73],精神方面也出现严重的药物依存性。尽管在妻子卡琳的支持下进入精神病院医治,但仍脱离不了对吗啡的依赖,甚至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这段时期是戈林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74][75]。
1927年秋,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对啤酒馆政变参与者施行特赦,戈林也因此回到了德国,再度进入了希特勒的政治圈中,两人也都同意这次要以合法选举的方式来取得政权[76]。1928年5月20日德国国会选举,纳粹党党员当选12席,戈林即为其中一人[77][78]。成为国会议员的戈林以其资产阶级的出身、功勋勋章的荣誉、幽默风趣的谈吐和具贵族教养的妻子等条件发展社交圈,进入主要为下层阶级出身的纳粹党员无法接近的上流社会,并快速拓展人际关系。纳粹党最大的赞助者——鲁尔工业巨头弗里兹·蒂森、克虏伯、梅塞施密特、德意志银行、BMW、汉莎航空、亨克尔纷纷捐钱给纳粹党,让后者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问题,特别是亨克尔和BMW还想请戈林担任特别顾问,额外再支付薪水,汉莎航空也为戈林提供事务所与秘书,钢铁制造企业还直接赠与戈林一栋位于柏林的豪华别墅[77]。后来在德国空军受到重用的埃哈德·米尔希即是在这时期于汉莎航空的社交圈上与戈林结识的,兴登堡总统和希特勒的首次会谈也是戈林的安排,尽管兴登堡心里蔑视希特勒,常私下称其为“波希米亚下士”,但他对于一战空军英雄的戈林却有相当的好感,因此与他会面的气氛都不错[79]。戈林在贵族圈中也颇有涉入,特别是维克托·楚·维德和奥古斯特·威廉·冯·普鲁士皇子与戈林私交最好[80]。
1930年,戈林成为希特勒的正式顾问,成为纳粹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930年9月的大选里,纳粹党一共取得了107席。1931年10月17日,卡琳去世,尽管戈林十分悲伤,但也相对在政治圈中越来越活跃。1932年7月31日的大选中,纳粹党取得了230席,超过社民党一跃成了国会第一大党[81],戈林也被任命为国会议长[82],也去接近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施加影响[83]。
纳粹党掌权后
[编辑]普鲁士总理与建立秘密警察
[编辑]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任命戈林在自己的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2月6日,普鲁士邦政府被解散,戈林被任命为该邦的内政部长,在这职务上,戈林先是解除许多共和派官员的职务,以纳粹党人取代,还组织由冲锋队、党卫队(最初为希特勒个人的安全卫队,在这时也充任保护纳粹高级官员的护卫)与“钢盔团”(亲纳粹的右翼政治团体)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将普鲁士邦的警察组织纳粹化。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鲁道夫·迪尔斯为普鲁士邦警察政治部门“1A课”(即后来全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前身)课长,迪尔斯当时虽不是纳粹党员,但因为做事精明干练而成了戈林的左右手。1933年2月24日,戈林命令警察少校瓦尔特·韦克筛选政治上忠于自己的400名警员,创立了“韦克特别警察营”(Polizeiabteilung z.b.V. Wecke),接着在克罗伊茨贝格近郊区设置了该营的基地,以盖世太保的逮捕部队身份活跃着。韦克警察营不久后又被扩编为“戈林将军邦警察团”(Landespolizeigruppe General Göring)、“戈林将集团军”(Regiment General Göring),在戈林成为德国空军总司令后,该单位亦转至空军[84][注 5]。
1933年2月27日,德国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迪尔斯迅速反应,断定为共产党人马里纳斯·范德吕伯所为,仅一天就逮捕了4,000名德国共产党党员[87]。现今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相依旧成谜,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党人策划了这场火灾,其中又因为戈林的国会议长官邸与该大厦有地道连结,嫌疑很重。这种流言也传进了戈林耳中,他反驳道:“对共党份子本来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哪需要什么特殊事件”“如果是我要纵火,我会烧比较不重要的建筑”,还曾以玩笑的口吻称“如果我要烧国会大厦,那我也不会说这是共产党干的,而会用完全不同的理由。因为国会大厦的会场实在是很丑,那里可是涂满了灰泥的墙壁。[88]”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大将提出证词,指称戈林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餐会上兴奋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89]”但戈林并没有承认此证言[90]。1933年9月,卢贝等五名共产党人于莱比锡的法院以纵火犯之名被起诉,戈林以检察官人证的身份出庭,但无法提出决定性的证据,特别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审理过程中,还因为该人巧妙的有力反击,还一度令戈林失态地大声咆啸[91][92],最终除了卢贝以外的四名共产党人都宣判无罪。
1933年4月10日,戈林自帕彭手中接任了普鲁士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该邦的国家代理官。1933年4月26日,戈林接管了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第8号的一家旅馆,将其改作新设置的“普鲁士邦秘密警察”(Preussisches 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为将该邦的政治警察统一打下基础,1A课也被吸收至此,成了该机关的核心部门[93],此一机关日后也就成了著名的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局长(Leiter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由1A课课长迪尔斯担任,戈林则自任秘密警察总长(Chef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94][95]。戈林想将盖世太保机关摆脱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同时,也正因为弗里克提出了“一体化”政策,将全国资源与机构整合、警察机关要统一的缘故,戈林还要面对来自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挑战,1934年1月时,希姆莱已经控制除了普鲁士邦和绍姆堡-利珀邦外的全德国警察机构[96],对戈林来说是个强劲的政治对手。1934年4月20日,戈林采取了行动,在盖世太保局长上面新设了名为“盖世太保监查官与代理指挥官”(Inspekteur und stellvertretender Chef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s)的新职务,并把这个职位给了希姆莱,等同是将盖世太保的实际指挥权转给了后者。
直到1935年11月20日为止,戈林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盖世太保最高领导人的身份[97]。普鲁士邦的普通警察也在党卫队的压力之下转到了德国中央内务部的管辖之下(德国内务部警察局长早期由希姆莱的部属库尔特·达吕格担任,到了1936年时由希姆莱自任,此时他已是全德国警察总指挥),而戈林的普鲁士总理、内政部长的地位即因而萎缩。戈林之所以转移盖世太保给党卫队的原因有许多种说法,如不想因为控制秘密警察而折损自己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对于作业严谨的警察事务已感到厌烦、认为迪尔斯不够无情、无法充分发挥盖世太保的机能来压制另一个危险的政敌组织——冲锋队[98]、拉拢党卫队至同一阵线、为打击罗姆进行准备等等的说法[94][99]。
此外,戈林还在1933年4月10日设置了情报机构“研究局”(后来又称“戈林情报局”),以其长时间监控政敌、国内外电报和破译密码等[100],此一机构在当时属世界上效率最佳、准确性最高的情报机关之一,在往后12年间制作了50万份监听报告[101]。后来研究局因开支过于庞大而被转到航空部之下,使用空军的军费。故此研究部成员也身着空军制服[102]。
“长刀之夜”
[编辑]
1934年6月30日至7月初,德国发生了针对由罗姆领导的冲锋队高层成员整肃谋杀的事件,通称“长刀之夜”,由戈林、希姆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相当于党卫队的第二号人物)和希特勒所主导[103]。长刀之夜首要的谋杀对象即罗姆,该人与戈林为政治上的竞争者,不仅在争夺未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之位,罗姆还常以其控制的突击队警察来威胁戈林的普鲁士邦警察指挥权[104],还曾于公开场合称戈林为“反动先生”,双方关系极为恶劣[105]。罗姆与部分突击队指挥官一直打着以突击队取代国防军、成为德国正规军的主意,这个目标使突击队和国防军之间闹得很不愉快。希特勒倾向国防军,也常被罗姆公开批评。对希特勒来说,冲锋队难以控制,且在他已取得国内政治独裁权时,已不需要这支政治斗争运动工具,仅是因为与罗姆有近10多年的交情而不愿摊牌。戈林与希姆莱见此,捏造了突击队准备造反、夺取政权的证据,说服希特勒尽快整肃突击队的必要性,希特勒也最终同意展开行动。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飞抵巴伐利亚慕尼黑,召集了罗姆以外的所有冲锋队指挥官,当场亲自整肃,接着驱车前往罗姆本人所在的巴特维塞。另一方面,身为普鲁士总理及内政部长的戈林、盖世太保指挥官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进行了柏林的冲锋队清洗行动。戈林派出韦克警察营直捣冲锋队本部,亲自现场指挥逮捕行动,将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们押至大利希特费尔德的普鲁士军官军校(戈林曾就读的学校)枪毙[106]。除了冲锋队外,还有好几位纳粹党的政敌与其幕僚也跟着被杀害。不过尽管清洗活动进行顺利,但比起戈林,党卫队与希姆莱更加活跃,为抑制后者,戈林放过了几个目标,包括西格弗里德·卡舍冲锋队中将、普鲁士皇子、外交部书记官伯恩哈德·威廉·冯·比洛[107]、前盖世太保局长迪尔斯(先前戈林掌握了他与冲锋队来往的证据,在长刀之夜前,戈林已将他贬为科隆的治安长官[108])以及德国副总理帕彭等人[109][110]。帕彭起初为各地突然展开的整肃感到疑惑,前往戈林官邸要求后者向他这位副总理说明,却突然被党卫队队员挡住了去路,这时戈林插手保住了帕彭一命[111]。戈林原先也想保留德国前总理施莱谢尔一命,不料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已抢先戈林和普鲁士邦警察一步,将其枪杀。不过另一方面,戈林与希姆莱对抗共通敌人时也不留余力,如在纳粹党中立场偏左的格雷戈尔·斯特拉瑟[112]、曾在啤酒馆政变中逃跑的卡尔也死于本次行动中。
7月1日,兴登堡拍了一份电报给希特勒和戈林,感谢两人在本次行动的表现[113]。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法院将戈林在长刀之夜的作为视作谋杀,对此,后者对美军心理分析官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反驳道:“听好了,对方可是变态的嗜血革命主义集团。纳粹党在初期大吵大闹、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打碎窗户的玻璃,让人们觉得该党是一群地痞流氓集团的元凶就是他们。他们还打算将德国军官团、党内首脑以及犹太人加以血洗。我认为消灭他们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被杀的就是我们自己了。[114]”
自然保育政策
[编辑]
1934年7月3日,戈林被任命为国家森林部长(Reichsforstmeister)与国家狩猎部长(Reichsjagermeister)[115]。戈林并非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争取狩猎部长一职。他热情地在这岗位上付出,令德国动物的滥捕和非法狩猎情况大为减少。1934年7月3日,戈林制定了《国家狩猎法》(Reichsjagdgesetz),为狩猎限制、保护与繁衍动物的法令,该法至今仍存于联邦德国。根据该法,狩猎必须经由政府进行严格的考核后许可才行,使用猎枪必须通过考试、猎犬也必须通过特定的训练,若最后猎补了超过配额数量的动物还会遭致严厉的处罚。为解除受伤的动物的痛苦,戈林规定猎人必须义务性地优先将其射杀,并禁止使用钢制补兽夹、投毒和在夜间使用探照灯等狩猎方式,对非法狩猎的惩戒也加重了,戈林的办公室里还贴有一张标语:“虐待动物的人就是在伤害德国人民的感情。[21][116]”,他个人也认为一个真正的猎人不仅应该同鸟兽作公平的较量,还要关心鸟兽的保育[117]。
不过戈林虽反对滥捕与盗猎,本人却也是个狩猎爱好者,在柏林东北的绍尔夫海德一地还有着私人的狩猎区,并于此地建造了“卡琳宫”,纪念因病而逝的妻子。不单是戈林本人经常在此地进行狩猎活动,他也常邀附近村民与好友使用该场地[118]。戈林在森林部长的职务上也对自然保育有相当的功绩,他实施于德国各大都市周围植树造林的计划,并规划绿化区,这些地区成了动物们的活动天堂以及劳工的休憩之地。在戈林就任森林与狩猎部长后数年,德国的森林维护与保育被称作是世界各国的自然保育范本[118]。1937年,国际狩猎委员会法国主席表扬戈林创立了“赢得了全世界钦佩”的狩猎法[119]。
成为空军总司令
[编辑]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内阁组成的同时,戈林被任命为国家空运专员;三日后,该职位改名为“国家航空专员”(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Luftfahrt);接着在5月5日,国家航空专员事务处升格为“国家航空部”,戈林即变成国家航空部长[115],此职位即是为日后德国重建空军时所预留的。戈林任命在社交活动上结识的米尔希为航空次长,两人即开始筹划规避《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发展空军的限制。另外,戈林还注重挖掘人才。他从陆军中选拔了诸如阿尔贝特·凯塞林、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和瓦尔特·韦弗等精英,也透过招募民间飞行员来培养新鲜血液,这些军官成为日后德国空军的骨干。戈林也邀请了一战时期的老战友乌德特加入德国空军,并请勒尔策担任“德意志航空运动俱乐部”(Deutscher Luftsportverband)会长,负责训练未来空军的飞行员[120]。
1935年,希特勒宣布德国将重整军备,德国将重建空军[121],戈林即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他在5月时晋升为航空兵上将,1936年4月晋升至大将,最后于1938年2月晋升为元帅。不过就实务面上,戈林并无投入多少力气在建设德国空军的工作上,也极少出现在空军总司令部办公室里。戈林的工作多由空军参谋长韦弗替他完成[122],据后者所言,戈林对空军发展最大的作用乃是争取预算[122],每当经济部长沙赫特提出预算争议时,韦弗直接将文件转交给戈林,后者随即去找希特勒,最终往往获得更多的预算。戈林曾说道:“元首对于我们(在预算要求上)如此的节制感到意外,他以为我会要的更多,总之记住一件事:钱不是问题。[123]”据资料指出,在1933年1月至1939年8月期间,德国共花费640亿马克在军备上,其中有40%是用在空军[123],占了极高的比例。戈林也对空军得以成为独立的军种有重要的作用[124]。基于上述,戈林在空军成立初期深受部属与参谋部军官爱戴[123]。
1936年6月6日,首任空军参谋长韦弗因飞行事故身亡,戈林随后任命凯塞林继任此职[125]。凯塞林任职后不久即与米尔希发生冲突。米尔希为平民出身,一战时曾为飞行员,战后成了民航人员,工作能力极强、揽权欲也很高。他对于掌控了航空部和空军总司令职务的戈林感到嫉妒,遂将野心转到了空军参谋长一职,处处刁难凯塞林,而该人也对米尔希报以歧视,认为他只是身着空军制服的平民。就此状况,戈林乐于见之且加以煽动,使两方无法威胁自己的地位[126]。凯塞林的继任对德国空军的建设有一点影响很大,他废除了韦弗先前极力推广的“战略空军”构想,将其下令研制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乌拉山轰炸机计划废除,认为资源不足的德国无力负担。当时米尔希与凯塞林的想法一致,而空军轰炸机总监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与空军参谋部作战处长保罗·戴希曼为了保全重轰炸机,要求由戈林来定夺。米尔希对戈林说道:“你有两种选择,是要生产1000架四发轰炸机,还是数千架的双发轰炸机?[127]”戈林并未想的特别多,他说道:“元首只会问我轰炸机共有几架,而不会问是哪种。[127]”就这样,戈林否决了戴希曼的想法,任凭米尔希把两种已准备进行测试的乌拉山轰炸机原型机变成废铁,德国也在二战全期再无发展出真正的战略轰炸机[127]。
凯塞林任职不满一年,因厌倦了整天在和米尔希作政治斗争,自行辞去了参谋长职务。戈林一度考虑请陆军的弗朗茨·哈尔德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继任该职(这两人后来分别成为陆军参谋长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在二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两人皆不愿与米尔希一起共事[127]。戈林因而任命施通普夫继任,但后者表示只愿意“暂时”接受[127]。1939年2月,戈林任命了年仅40岁的汉斯·耶顺内克为空军参谋长,前者认为年龄较长、经验与实务丰富的空军将领们不易与自己妥协,因而安排了年轻、能力强、听话的参谋长[128],但耶顺内克因其资历浅而经常被高级将领所轻视,在诸多决定上必须让步,且戈林经常将四周的空军友人(勒尔策、博登沙茨、飞行训练学校教官阿尔弗雷德·克勒等人)视作顾问团,令耶顺内克工作格外地困难[128],加上该人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与观点几乎不以自己空军参谋长的专业眼光审视[129],亦为日后德国空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戈林另一项重大人事任命是把乌德特拉拢过来制衡米尔希,于1936年初任命其为战斗机与俯冲轰炸机总监,4个月后又让他担任了“空军技术处”处长,负责新型飞机的开发与采购[130]。这道任命很大程度上是不适任的。乌德特的教育背景、资质与性格不具有担任如此高阶职务的能力,却要直接负责手下超过26个部门[131],不仅使原先尚属效率颇高的德国空军流于官僚化[130],在诸多机种的生产和研发工作上也出现重大疏失。
总体来说,戈林对于德国空军初期的快速发展可说是有益的,但长远来看却是灾难性的[132]。戈林的精神框架仍局限于一次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他在补给、后勤、战略、飞机性能、技术与工程等诸多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空军的全部核心因素)几乎可说是无知的[132],但他又因为与希特勒密切的政治关系而不会被撤换,致使德国空军在进入战争的考验时暴露出一连串领导层的缺失,这方面戈林有很大的责任。
经济巨头
[编辑]
戈林在德国经济面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权力与影响之大而被人称为德国的“经济沙皇”[133]。1936年8月时,希特勒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拟出了“四年计划”,于同年9月9日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发表。计划主旨为德军必须有在四年内发动战争的能力,德国经济必须能予以支持,而戈林即在1936年10月被任命为本计划之总负责人。
戈林主导的战略以提高资源自给率和军需供应为主,这使得国家债务大幅增加、国民生活水准增长率减半、转向战时经济体制[134]。四年计划中,戈林与法本公司行政总裁——卡尔·克劳赫关系最为紧密,计划资金约有三分之二由法本公司相关人员所分配[135]。由于德国当时的钢铁生产深受铁矿石产量不足所困扰,因此出现了反对四年计划、希望自外部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声音,为此,戈林在1937年6月16日宣布将开采国内铁矿石,并将以此为基础,建设成套的钢铁生产体系。7月15日,政府拨下了资金500万马克,于萨尔茨吉特一地建造了“赫尔曼·戈林矿产-制钢工厂”,戈林也与德国大型钢铁企业,如“联合制钢”等公司达成合作共识[136]。
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期间,戈林还取代了亚尔马·沙赫特,担任德国经济部长,使经济部成为四年计划的执行机关[137]。1938年2月,在资助更多资金后,“赫尔曼·戈林矿业-制钢工厂”成为了德国仅次于法本公司和联合制钢的最大企业,同年7月时更扩建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成了一家集矿业、制铁、武器、机械、内陆水运等部门的工业巨头[136]。
布隆贝格-弗里奇丑闻事件
[编辑]
长久以来,戈林就因为觊觎国防部长的职位而敌视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元帅,也一直在暗中找机会破坏其名誉。布隆贝格是一位六十岁鳏夫,后来与他的年轻女秘书坠入爱河。但布隆贝格的对象有他人一直在追求,使其相当烦恼,便与社交上相当活跃的戈林商量此一私事[138],戈林便以其能力将追求者送到了阿根廷去[139]。不久,布隆贝格就和其对象完成了婚事,戈林是证婚人之一[140]。1937年1月21日,有人向柏林陆军总司令部告密布隆贝格夫人是一名妓女[141],致使柏林警察调阅档案,发现布隆贝格夫人年轻时曾因为贩卖情色照片而在警察局留有纪录[142],此资料先传到凯特尔处,后又到了戈林手中,最终布隆贝格自行请辞了国防部长职务[143]。
戈林在1937年结束时对出任此职抱有强烈的希望,但在他之前还有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挡在前面,为其权力争夺的大敌,且该人和布隆贝格一样,认为戈林指挥下的空军在战争中不会有实质的作用,遂为戈林所怨恨,找机会将他除去。适逢盖世太保从一位诈欺犯口中得知弗里奇为同性恋(这在保守的德国军官团中是无法容忍的)[144],戈林在处理布隆贝格事件的同时,也将同性恋丑闻一事要求希特勒处理。希特勒要弗里奇辞职,而弗里奇则要求召开荣誉法庭处理,戈林则变成弗里奇的主要指控人[145]。虽然法庭最终恢复了弗里奇的名誉,但希特勒已决定另外任命他人继任,而弗里奇已失去继续担任高级职位的机会。不过对于戈林希望兼任陆空两军总司令的要求,希特勒相当干脆地回绝了。他最终任命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为陆军总司令[146]。
为了安抚戈林的失落,希特勒于1938年2月4日把布隆贝格的军衔——元帅授给了他,并在隔天才宣布由希特勒自己继任布隆贝格原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47]。
活跃于外交事务
[编辑]

戈林反应灵活、幽默和颇具贵族气息的兴趣,总使他在外交活动上无往不利,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生性激进的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还要受欢迎。在战前,戈林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英国哈利法克斯伯爵、驻德大使内维尔·韩德森爵士之间的私人关系都还不错,并与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谈判和直接主导了德奥合并事务、促成德军介入西班牙内战和解决捷克的苏台德问题,此外,戈林也奉行促成英德联盟的主张,甚至多次私下曾说过“德国不愿看到英国被削弱”、“必要时将会予以援助的”一类发言[148],尽管最终两国还是走向战争。
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分作叛军“国民军派”与政府军“共和派”两势力。其中,国民军的佛朗西斯哥·佛朗哥将军向德国求助,尤其是空中兵力方面。布隆贝格、希特勒和戈林在会议上基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决定介入其内战、协助国民军。西班牙的战事给了戈林可以绕开外交部和经济部、增强影响力的机会。戈林主张布署大规模德国空军部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试验机会。之后,因为德国空军远征部队“兀鹰集团军”受佛朗哥将军指示而轰炸了格尔尼卡,导致戈林的声誉到严重影响。国际上的左翼团体将此轰炸比为典型的纳粹恐怖事件,而戈林原本和英国之间尚算良好的关系也受到重创。他因此不得参加1937年5月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后来国防部长布隆贝格代表出席)[149]。
戈林身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深为德国资源不足所烦恼,因而积极推动和奥地利合并的计划。奥国的施蒂利亚州盛产铁矿,也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工。希特勒也表示支持。1938年2月12日,戈林与奥国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会面,表示若非和平统一,将会动武入侵奥国。后来奥国因而容许纳粹党合法存在,并预计于3月举行关于合并议题的公投。然而希特勒不愿公投,戈林因而打电话给奥国总统威廉·米克拉斯,要他换下舒施尼格,并终止公投行动,否则德军将武装入侵,奥国内部的纳粹党份子也将引发暴乱。米克拉斯接受了戈林的要求,舒施尼格于3月11日被免职,公投也跟着被取消。第二天早上5点半,德军开进奥地利城内,路上毫无抵抗[150]。德奥合并完成后,戈林继续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接待外国宾客,有技巧地宣传德国的军事实力。戈林巧妙地安排英法代表团观看德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与优秀的飞行员,而对一些内在的缺点则尽量隐瞒,同时也多次声明德国不要战争,只是必须保护自己[151]。戈林的作法颇有成效,外国访客多为他的态度诚恳和德国的军备“强大”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对法国起的作用特别大,进而连带影响了英国的判断。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白也对德国空军深表敬畏,他接受了戈林授予的带星“德意志鹰勋章”,并在回国后成为宣传孤立主义、避免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的重要人物[151]。
奥地利之后,希特勒急于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戈林便在私人外交场合上测试英法的态度,还力促匈牙利煽动捷克内部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制造暴动、透过经济手段压迫捷克[152]。在局势逐渐紧张时,英法寄望戈林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戈林也因而应韩德森与法国驻德大使安德列·法朗斯瓦-朋西的要求去劝希特勒信守谈判内容,却因而遭到希特勒的白眼[153],随后被贴上中间派的标签而遭到冷落。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于柏林总理府接见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威胁后者德军将开进捷国,不得抵抗,戈林也帮腔德国空军会轰炸布拉格,导致哈查一度心脏病发,后被戈林带来的药剂救活[154]。哈查后电告布拉格方面,希特勒成功夺占了捷克全国领土。然而希特勒驱车前往布拉格时,陪伴的不是戈林,而是里宾特洛甫。1939年5月22日,德义签署《钢铁条约》,戈林同样被冷落[155]。
1939年下半,欧陆再度战云密布,有一位和戈林交情不错的瑞典商人比耶·达勒鲁斯想透过非官方的方式来阻止战争。达勒鲁斯认为纳粹政府并未理解英国与波兰结盟的意义,他想透过戈林这一管道和希特勒接触与交涉,尽管他直到战争爆发后几天都作为中间人而来回奔波于英德之间、一再尝试让戈林访英、会面英国驻德大使商讨等等,但一方面戈林无法影响希特勒的抉择,一方面又对此事显得不感兴趣,最终仍未能阻止战争[156]。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对德波局势的演说,并正式宣布戈林为其接班人[157]。
第二次世界大战
[编辑]战争爆发到敦克尔克撤退
[编辑]
德军对波兰的战事势如破竹,一个月内即摧毁了其武装部队,并轰炸了首都华沙。尽管戈林在许多场合装腔作势,发表许多好战与夸张的言论,在另一方面也不时流露出对于这场战争的厌恶,这使其与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哈尔德、埃尔温·隆美尔等职业军官之间相互蔑视[158]。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提供的资料,戈林在德军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月“假战”中,曾秘密保持着几条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联络的管道,也透过了驻墨西哥的代理人——乔吉姆·赫茨莱特,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进行过几次会谈,力促达成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和平。除了公开宣称或私下与其协商的动作,戈林甚至还向英国人暗示,他本人愿意自希特勒那里接管德国的实权,他也将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军将撤出波兰“非德国领土”、希特勒也会变成类似“总统”的角色[159]。不过,戈林这些外交上的努力被英方所拒,后者明确表示,除非收到希特勒政府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他们才会谈判。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则冷淡地暗示,他们希望能发生重大的内部变动[160]。
1940年春季,德军打破假战、发动西线攻势。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很快地摧毁了比利时的埃本-埃美尔要塞、并空降至荷兰夺取战略据点,地面部队也受其支援、快速挺进。总体来说,德国空军在西线战斗中发挥了至关的作用[161]。然而就在英法军队被德军围困于敦克尔克时,戈林视其为空军立功的绝佳机会,他向希特勒保证“单凭空军即可将敌军歼灭”[162],而希特勒可能是出于保护即将用于攻打巴黎的装甲部队等原因(有许多说法,参见敦刻尔克战役一条目),同意由空军进行该任务,戈林甚至还建议装甲部队撤远一点,以免被飞机投下的炸弹所伤[162]。米尔希、凯塞林、约德尔都对此反对,甚至当陆军将领通知里希特霍芬其坦克停止前进时,后者还打电话到耶顺内克去要求将命令取消“坦克若不再前进,英国人就要逃走了。没人真的相信我们可以从空中阻止他们!”耶顺内克应道:“你错了,铁人(指戈林)相信它(德国空军)可以![162]”最终,德国空军仍无法歼灭盟军部队,共有338,226名盟军借由海路撤退至英国本土,仅俘虏了40,000名法军[163]。敦克尔克之战不单是德国空军威望的一次重挫,也被认为是戈林在战争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162]。
虽然英国尚未投降,但希特勒已为西线战役的成功而庆祝,他于7月19日将戈林晋升为特别设置的军衔——“国家元帅”,超过了过去德国历史上最高阶的“元帅”军衔,同时授以“大十字勋章”,该勋章和军衔在二战中仅戈林拥有[164]。除了戈林外,空军的凯塞林、米尔希、施佩勒三位空军将领也都被晋升为元帅[164]。
不列颠空战的失败
[编辑]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即将展开对英国本土的作战,必要时占领其全国。但戈林本人则从希特勒那里得知打算透过外交恫吓的方式促成和平,因此戈林并未要求空军参谋部认真制定作战计划。戈林在亚洲号列车上向空军将领们作战会议时,他说道:“英国已经在敦克尔克筋疲力竭了”[165],之后受到了米尔希的反驳:“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国家元帅阁下,只要给英国三周的时间,他们就能卷土重来![165]”尽管戈林首先当下的是拒绝此意见,但会议中又为其所说服[165]。受到戈林的极力吹嘘影响,希特勒决定自空中发动毁灭英国的作战[166]。戈林本人是空权主义者,对于意大利朱利奥·杜黑提出的《空权论》,即单凭空中武力即可赢得战争的想法深信不疑,也因此他相信德国空军可以独自击败英国[167]。但另一方面,戈林还保持着一次大战的空战观念,轻视雷达与机群长距离作战造成的诸多问题,使德国空军承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至8月下旬,戈林一直轰炸英国机场与港口,望以此令英国屈服。然而8月25日,德国柏林受到英军轰炸机的攻击,希特勒因而震怒,要戈林对伦敦发动规模数倍的报复性攻击。戈林对此命令感到困窘,他向希特勒表示对伦敦的轰炸前提是必须瓦解其破坏机场,希望将轰炸目标转为伦敦周围的军事设施,但后者基于政治与复仇的理由,坚持对伦敦本身进行轰炸[168]。戈林请求希特勒再度考虑,说道:“这个作法对荷兰人可行,但对英国人没辙。”、“即使攻击伦敦也无法令英国人屈服。”但希特勒依旧故我[169]。德军对伦敦的攻击就此使不列颠战役的结果扭转,德国空军的损失开始攀升,战况变得更为不利,适宜进行两栖登陆的季节也逐渐过去,1940年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进攻英国本土的“海狮作战”无限期推延[170],准备向东方的苏联进攻,对英国则持续施以战略轰炸到1941年5月[171]。
不列颠战役的失败对戈林的威望是一次打击,不仅是空军的实力消耗了许多,戈林的侄子彼得(Peter)也在10月13日阵亡[172]。德国空军在此战中暴露了许多严重的军备生产问题,飞机产量时好时坏、长远的研究与发展计划被草率取消[173],后来在苏德战争中更成德国空军的致命弱点。为解决对英战争,除了空中轰炸外,德军亦进行海上的破交战,派出巡洋舰与潜艇在海上攻击同盟国商船。然而因为戈林对德国海军抱有相当的敌意,在许多方面上采取不合作或几近妨碍的态度,两军种的协调能力很差[174]、也缺乏鱼雷轰炸机[174]。对于海军想建设海军航空兵的主张,戈林明确地表示:“任何会飞的东西都由我来管![175]”在1941年2月4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对希特勒抱怨英军轰炸机持续攻击北部沿海而无受损失,后者因此将第40轰炸机联队交给德国海军指挥。戈林闻讯后极为愤怒,他向海军潜艇司令的邓尼茨骂道:“你可以搞清楚一件事,只要我还活着,或说我还没辞职之前,你们的雷德尔元帅休想得到一支海军航空兵![176]”另外还补充道即使是邓尼茨控制了该单位,他也不会让其获得任何长程飞机的补充[176]。正因如此,后来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役时,潜艇总是饱受无侦察机可用的困扰[175]。
由盛转衰
[编辑]
尽管戈林反对侵略苏联、多次以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故事企图说服希特勒[177],但均未奏效,也不敢直接反驳后者,仅私下向手下参谋军官约瑟夫·卡姆胡伯抱怨[178]。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作战”入侵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戈林的空军同样势如破竹地攻击苏联空军,摧毁了大量飞机。戈林在幅员逐渐扩大的德军占领地掠夺著苏联的资源、榨取乌克兰的粮食、向希特勒建言将波罗地海地区并入德国(以供狩猎用)、还曾在指挥部说过德国空军可以轰炸苏联城市,好降低斯拉夫人的人口[179]。
1941年9月起,苏军抵抗转为强烈,俄国战场天气也开始转为寒冬。尽管德军仍克难地往俄国腹地深入,但空军后方已呈混乱状态,对开战时间的估计错误使德军只有各种不适宜的管理计划来维持当前战争之所需(参见纳粹德国空军条目的“疏忽与失败”章节)。戈林本人也只关心作战的飞行员、对于地勤人员不放心力,后方作业都丢给了行政能力较差的飞行员处理[180],其中最为著名者即戈林的一战老友乌德特。在战争逐渐长期化后,身为管理飞机生产的乌德特业务逐渐增多,加之体制凌乱且非其所长,后更成了希特勒和戈林转嫁对德国空军不满的出气筒,最终心理压力不戡负荷而于1941年11月17日举枪自尽,死前还留下“铁人(戈林的绰号),你抛弃了我”的遗言[注 6][183][182]。
1941年12月,莫斯科前线的德军遭苏军大规模反击,不得不后撤重整战线。1942年中,德军发起以南俄高加索一带的油田为目标的夏季攻势[184]。在挺进的过程中,希特勒的目标逐渐自油田转向伏尔加河畔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大量投入军队去夺战此城,但1942年11月,德军第6集团军被苏军发动的“天王星作战”而受到包围。在希特勒决定第6集团军是要突围还是固守时,戈林向他保证可由空军对第6集团军进行每天300吨的空运补给,希特勒因而下令德军就地固守斯大林格勒,但实际上德国空军根本办不到补给整支集团军的任务,最好的状态下一天也才成功投送约120吨的物资[185][186]。原第6集团军共285,000人的大军仅剩91,000人存活,集团军长弗里德里希·包路斯元帅于1943年2月上旬率部向苏军投降,斯大林格勒之战就此结束,成了二次大战重大的转捩点[187]。

在德军于东战场受挫的同时,其他战区局势也逐渐倾向盟军。北非战场上,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非洲军部队深受补给不足之困扰,戈林再度保证运补资源却又食言,深为隆美尔所痛恨[188]。西线的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实力也正逐渐增强,开始选择德国指定目标执行作战。1942年2月13日,英美联军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约数十万人伤亡。5月30日,英美联军发起了首次对科隆的千机大轰炸[189]。1943年7月24日,汉堡市遭到毁灭性轰炸。德国空军不仅无法阻止英美轰炸机将德国一座座城市化为废墟,还一再损失难以取代和补充的机组人员,同时由于盟军对德国炼油厂和铁路通信等地的攻击,持续削弱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190],戈林的声望因而逐渐滑落、饱受德国平民的指责[191],也与战斗机总监阿道夫·加兰德的关系严重恶化。1943年8月18日,戈林的另一位同僚——出任空军参谋长达四年之久的耶顺内克将军自杀身亡,留下“我再也无法与国家元帅共事了![192]”的遗言。
军事面外,戈林在政治与权力上也逐渐被边缘化。自1942年起,阿尔伯特·斯佩尔被希特勒任命为军备部长,与戈林的职权有所重叠,导致后者权力遭到削弱[193];1941年独自飞往英国谋和的德国副元首赫斯的继任者——马丁·鲍曼也是戈林政治权力的竞争对手,在戈林处于低潮时常在希特勒耳边加以中伤,进而影响了希特勒对戈林的评价[194]。尽管戈林仍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和空军总司令,但希特勒在军事会议上也不再要戈林出席[195]。由于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无所事事的戈林开始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他数量众多的私人别墅中[196],指挥部队去占领区掠夺他国财产,或用国库公款去搜刮美术品[197],也常以“身体欠佳”为由隐退会议[198],对于德国逐以恶化的局势则采取放任与逃避态度。
1945年4月20日,戈林出席了希特勒在柏林举行的生日会,离别后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从此他再也未见过希特勒[199]。
被捕
[编辑]1945年4月23日,逃出元首地堡的德国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航空兵上将,带来了约德尔的口信给人在萨尔茨堡别墅的戈林,表示“元首意志坚决……与盟军谈判的事务宜由戈林进行。”科勒也对其怂恿:“是时候该行动了,国家元帅阁下。”然而,戈林怀疑此口信出自于政治仇敌鲍曼所设的陷阱。戈林因此想先确认希特勒是否同意将指挥权转让给自己,于是找来了总理府秘书长汉斯·兰马斯,询问希特勒在1941年6月29日公布的继承法有效性。兰马斯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迷惑的戈林于是向柏林的元首地堡拍发了下述电报[200]:
接到这封电报的鲍曼煽动希特勒“戈林有叛变的意图”,后者怒不可遏,下令将戈林逮捕、开除党籍、关押到别墅里。另一方面,此时的戈林正与同样躲到别墅的元首办公厅主任菲力普·鲍赫勒草拟给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亲笔信,忙得不可开交[204]。4月23日下午9点,收到鲍曼发出的命令电报后,伯恩哈德·弗兰克党卫队中校率领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队士兵包围了戈林一行人所在的别墅,戈林的家人、随从与部下都被监禁[205][206]。然而在4月25日,萨尔茨堡受到盟军空袭,戈林的别墅与贝希特斯加登的设施都被烧毁,故戈林一行人改迁至山腰的防空洞里避难,党卫队将戈林与其家人分离,连交谈都被禁止[207]。戈林找来法兰克,希望他能向希特勒传达自己愿遭枪决、请放过他的家人与随从的要求[207][206]。戈林向党卫队表示,贝希特斯加登已不宜久留,不如转往奥地利的毛特多夫堡(戈林小时候曾在这里住过教父的城堡),获准后,戈林家人和随从们同党卫队的车队往毛特多夫堡前进[208]。途中听到了汉堡电台发布的消息:“赫尔曼·戈林国家元帅心脏病发作,状况危险,因此他已向元首辞去空军总司令职务。元首接受其辞职后,任命空军大将罗伯特·冯·格莱姆为空军总司令,同时也晋升为空军元帅。[208][209]”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戈林被解除职务的同时,也不再具备其接班人资格,改由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继任(职位为联邦大总统,而非元首),同时也再度痛斥戈林“德国空军之所以失败,完全是戈林的责任。[210]”当天,党卫队司法参谋之一的恩斯特·布劳塞(Ernst Brausse)上校给戈林过目鲍曼的电报,内容写道“若国家要灭亡,必须立刻处决掉4月23日的叛徒。[211]”戈林愤恨地说道:“又是鲍曼搞的鬼![211]”。5月1日,身在毛特多夫堡、透过无线电广播得知希特勒死讯的戈林向埃米说道:“希特勒死了啊……我已经无法告诉他到最后一刻我还是对他忠诚的……[212][208]”当天,布劳塞打电话给德国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请示是否该处决戈林。凯塞林建议别这么做,但也不想就这样放他走,于是把这问题丢给了邓尼茨,后者并未回复[211]。最终,凯塞林于5月6日决定解除了戈林的监禁,将他交给德国空军[211][210]。同日,戈林向人在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拍发电报,表示“听说您要派遣约德尔去和艾森豪威尔谈判?比起他,我更能胜任‘元帅对元帅’的谈判,使德国获得更有荣誉的和平。”但这通电报被邓尼茨所无视,戈林没有收到任何回应[213][214]。
向美军投降
[编辑]

虽然未得到邓尼茨的许可,戈林依然想促成他的元帅会谈。5月7日,戈林转移到滨湖采尔附近的菲施霍恩,派遣空军上校的副官为美军的特使,身负要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戈林会谈要求信,以及一封要交给当地的美军部队司令,请求后者可以保护自己(戈林)不被党卫队及盖世太保所害的信件[209][214]。但是副官在那里等了许久都不见美军的踪影,不耐烦的戈林便驱车出发去和美军接触。不久,美军抵达了滨湖采尔,于雷德斯塔特附近的山路中找到因为难民而被交通阻塞、动弹不得的戈林,随即将其逮捕[215][216][217]。
起初,美军给戈林享有VIP般的特别待遇,不仅允许其暂时回滨湖采尔,还可与美军准将罗伯特·斯塔克(Robert Stack)共享晚宴[218]。隔天,戈林被带到基茨比厄尔的美军第7集团军司令部,美军陆军航空军将领卡尔·史帕兹上将前来向他致意,开了香槟酒招待他,为他们在天空的英勇、果敢而干杯[219],晚上还为其举办欢迎宴会[218][215][219]。艾森豪威尔闻讯后大发雷霆,下令对戈林以一般战俘的身份处置[215][219],此后戈林的生活便转为严峻。第7集团军司令部立即向戈林没收了元帅杖、所有的勋章和钻石戒指[218][220],之后将他送到美国人称“垃圾箱”的蒙多夫战俘营[213]。
戈林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冷淡后感到很失望,“元帅会谈”已不可能了。美军已在奥格斯堡对戈林做初步的讯问,一位情报军官描述戈林:“与谣传的相反,戈林远未到精神错乱的程度,事实上,他应算作一个非常精明的家伙、一个杰出的演员、老奸巨猾,他总是将自己的想法有所保留,以便日后可以拿来讨价还价。[221]”5月21日,戈林被关进卢森堡蒙多夫的公园饭店(Parc Hotel)的一个房间,在那里过了四个月的时间[222][223]。之后该地又关进了邓尼茨、凯特尔、里宾特洛甫、斯佩尔、凯塞林、帕彭、沙赫特、罗森堡、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等人[224][225]。
由于一天内接受长达6小时的盘问、简素的饮食和禁服吗啡等因素,戈林的体重一口气从127公斤,瘦到约91公斤[226]。令戈林自吗啡中毒中解脱的是美军精神科医师——道格拉斯·凯利少校,据后者所言,戈林并非真正吗啡重度上瘾者,只是有服用的习惯,疼痛很容易用温和的镇静剂就消除[227]。在此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为审判含戈林在内的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迅速制定了溯及法《纽伦堡宪章》,规范了犯罪的定义、法庭结构、诉讼流程、惩罚等[228]。随后,美国提议在美军占领的纽伦堡进行审判,而苏联则提议在自军占领的柏林进行,最终美国的提议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持,以三比一意见决议于纽伦堡开庭[228]。
纽伦堡审判
[编辑]开庭前
[编辑]1945年9月,戈林被转移到美军管理的纽伦堡监狱[229]。纽伦堡审判分作“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起诉罪名,而戈林在这四方面都被起诉[230][231]。审判前戈林阅读了自己的起诉状抄本后说道:“我不认为这起诉有什么根据,这场审判里,比起律师,请的翻译更重要。[232]”监狱里的美军心理分析师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上尉和凯利少校要戈林对起诉状发表下感想,戈林则写道:“胜利者永远是法官,败者永远是被告”[231][233]。
吉尔伯特在开庭前给所有被告做了一次美国的“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检查”,结果显示戈林智商为138,与邓尼茨同为全被告中第三高智能者(第一高的是前经济部长沙赫特,但考虑到该人的高龄条件,此数值多少有灌水,而第二名则是前荷兰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234]。
检察官起诉
[编辑]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开庭,法院在决定被告席座位时,决定将戈林排到第一列最左端的一号被告位子,而非希特勒正式继承人的邓尼茨坐那个位置[236]。第一天,法院只进行了宣读起诉状的程序。11月21日,针对起诉状的内容,被告开始进行抗辩。戈林说道:“在表示有罪或无罪之前,我有事情想说。”打算马上进行一场演说,但首席法官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将他打断:“请被告立即回答有罪还是无罪。”戈林的回答是:“就所控内容而言,我宣布本人无罪。”在其他被告都做完抗辩后,戈林径自走到麦克风前想要说话,而劳伦斯再次把他打断:“你现在不许在法庭上发言。[237][238]”
接着就是长达4个月的检方发言,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检察官宣读证据文件、告发、观看纪录片、传讯证人等等,在此期间被告不得发言[230][239]。检方主张戈林为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准备、于占领地进行压榨、在集中营把犯人用作奴隶、迫害犹太人和夺取其财产,以及对海德里希下达有系统灭绝犹太人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等方面的主谋[240]。11月29日,美国检察官团播放了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的纪录片,而戈林则是打哈欠、漫不经心的观看[241]。影片结束时,戈林闷闷不乐,他抱怨道:“在奥地利案子时我们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指法院指控德国“入侵”奥地利一事),可是那影片把一切气氛给毁了[242]”。12月11日,美国检察官团又播放了一部影片,这次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将涉入此案的军人带去罗兰德·弗莱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影片,影片中弗莱斯勒指控被告时咄咄逼人、用尖叫和怒吼对后者羞辱,戈林在被问到看完影片的感想时说道:“那集中营的影片就已经够糟了,还有什么更伤我的心吗?就是弗莱斯勒那张大嘴巴,那家伙对被告尖叫的样子令我毛骨悚然,那些被告都是德国将军,还根本没有被定罪,我为此觉得羞耻得要死。[243]”

戈林也对其他被告施加强烈的影响力。被告们以其各自在第三帝国的地位与个性分成了许多个小圈子(除了疯狂的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无人想搭理,欲加入任何圈子都被无视),而戈林以其身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二号人物身份,自认为所有被告的领导人,他给予每个人被告许多建议,并试图组成一个拥护纳粹与希特勒的统一战线[244]。
不过,其中一名被告——前军火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对戈林的战略不表认同,他已决定承认自己在希特勒和纳粹上相关的罪行。1946年1月3日,斯佩尔的律师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了党卫队保安处国内情报组组长奥托·奥伦多夫少将,在对后者的提问中,暴露了斯佩尔曾有暗杀希特勒的企图[245][246]。戈林因此被激怒,休庭后他跑到斯佩尔面前骂道:“为什么要把这种逆贼的事情讲出来!?我们的统一战线都被你打乱了!”但斯佩尔很冷静地将戈林推开离去,后者随即被卫兵架住逐回[245][246]。
此后斯佩尔和戈林(还有纳粹和希特勒)诀别。斯佩尔告诉吉尔伯特,戈林在与其他被告一起用餐时会威胁他人,提议将戈林隔离。吉尔伯特向典狱长布尔顿·C·安德鲁斯上校报告此事,后者因而命令戈林在2月18日只得自己一人用餐[247][248]。
被告方辩论
[编辑]辩方质问
[编辑]
1946年3月8日,法庭开始了戈林律师的辩护,而到了3月13日,戈林本人到发言台开始为自己辩护,这一天是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高潮[249]。
首先,以施塔默质问戈林的方式开始,刚开始戈林声音有些紧张、手也在颤抖,但在约10分钟后,戈林的讲话已回复正常,开始流利地讲述纳粹党的历史、希特勒的形象、在相同立场里得到的经历与经验等等,其声音宏亮、内容钜细靡遗。戈林的演说长达20分钟之久,并获得了在场的人的敬佩。当法庭退庭时,邓尼茨向斯佩尔说道:“你看,连法官都被感动了。”后者也表示这是一场“好的演说”[250][251]。《纽约客》杂志记者对戈林评价道:“在这个人才平庸的历史时期,(戈林拥有)这一时期最睿智明达的一个头脑。”但该人同时也表示戈林“聪明睿智,却无良知”[252]。
3月14日,戈林发表演说,欲使“领袖原则”正当化:“直到现在,我仍是积极支持着领袖原则。别忘了,各国政治结构的起源与发展迥异,在某国可行的政治制度,并不适用于另一国。德国数世纪以来都是君主制、走在领袖原则之下。因此我必须——特别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排除一切困难,使领袖原则成为德国唯一的正道。”“领袖原则并非纳粹党特有的产物,天主教教会和苏联政府都建立在与此相同的基础上。[253][254][255]”同日,戈林宣布反犹太法——《纽伦堡法》是在其身为国会议长时公布的,他说道:“这道法案的发布、施行、获得元首的命令等等,我全部承担其责任。上面还有着我的签名,是我发布的,我有责任,我不会以此逃避自元首那里获得的命令。”表示其承担全责[250][256]。另一方面,戈林还主张反犹太法案的制定,是因为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财力和权力,必须加以限制[255]。盖世太保方面,戈林主张至少在自己指挥的任期中,其若犯了出格的行为,都有施以处罚[253]。
3月15日,戈林还主张1940年进攻荷兰时,德国空军轰炸鹿特丹一事纯属意外,而从占领地大量搜罗艺术品,是为了“在战后或我认为某个适当的时候,创办一座美术馆,向德国人民展示这些艺术珍品。”在提到战争中必须遵守交战规定、德国是否与同盟国采取不同的行动时,戈林答道:“《日内瓦公约》与《海牙公约》早已被现代战争所彻底践踏,在这里我要引述我们最大、最强以及最重要的敌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在真正的死斗中,法律是不存在的’。”听到这里,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之后,法庭向英国政府发电查询,丘吉尔在何时何地说过这句话。英国外交部回应,丘吉尔曾在1940年担任海军大臣时说过:“在死斗里,若侵略者将人道完全践踏,而抵抗方却要因为早已被破坏的条约而被束缚著,那正义将不复存在。”尽管戈林在引言上有部分错误,但其情绪甚为接近[257]。
辩方质问至此结束,周末时要开始进行检方诘问程序,由戈林与检察官直接交锋[258]。
检方诘问
[编辑]
3月18日上午,其余被告的律师上前向戈林询问如何使自己的被告脱罪的问题,而戈林表示准备承担所有一切责任[259]。3月18日下午至3月22日,由检方进行盘问[260][261]。
首先由美方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开始提问,纳粹党图谋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是否为真?戈林则再次强调德国没有无用的民主主义,只有以领袖原则为基础的政体。杰克逊接着以侵略苏联的相关问题来对付戈林,却适得其反,让后者有力地证明自己并非侵苏战略的支持者[260]。接着,杰克逊向戈林质问关于后者计划“解放莱茵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问题,而戈林纠正了杰克逊手中的那份计划,表示事实上不是“莱茵兰”,而是“莱茵河”,不是“解放”,而是在战时动员时清除河道上航行的障碍物,结果戈林是正确的。但杰克逊认为这是将莱茵兰重新武装计划的一部分,他追问“之所以要对外国保密,是不是就是因为此计划具侵略性质呢?”,而戈林则反唇相讥:“我可不记得在报刊上看过美国公布自己的动员计划![262]”杰克逊受此一反击而乱了方寸[263]。但到了隔天,杰克逊针对犹太人遭到迫害与掠夺艺术品、粮食、资源等问题盘诘戈林时,反变成后者招架不住的窘境[264]。
至于问到了海德里希的命令书——《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时,戈林主张不是“最终解决”而是“全面解决”,不是要把犹太人都灭绝,而是要把他们从东欧转移出去,否定了犹太人灭绝计划的存在和自己从中扮演的角色[265]。在这之后,杰克逊指控德国空军空袭华沙时轰炸了美国大使馆,并拿出了一张“由德国空军拍摄”的照片来当作证据,不过却被在一次大战有丰富航空摄影经验的戈林指出,此照不像是在飞机上拍摄,倒像是在高塔上拍摄的作品,而且这张照片背面没有日期、没有地点、没有身份证明、没有鉴定,根本不配作为法庭上的证据[266]。杰克逊接着又转问德国将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处决的问题,但其语调无力而单调。最终,杰克逊与戈林的交锋在不甚重要的签名真伪争论上结束[266]。法庭上的人都认为,杰克逊的盘诘欠缺技巧,戈林因而得到了相当大的反驳机会[267],且戈林听得懂英语,而杰克逊却不懂德语、必须仰赖翻译,戈林即能利用这时间差仔细盘算如何应对、慎重地给出答案[260]。加上杰克逊虽然对德国历史学而有成,却缺乏许多细部的知识,常被戈林揪出指正[267]。总结下来,杰克逊无法决定性地盘诘戈林[260],反常被其驳倒,还曾情绪失控地摔耳机,冲口说他应付不了戈林,使法庭不得不休庭[265]。
3月20日,由英国首席检察官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伯爵出庭盘问。法伊夫提问速度极快,快得戈林的翻译跟不上,常在戈林刚回答完问题后立刻丢出下一道问题,庭长必须提醒法伊夫放慢速度,但这样的盘诘方式却显得十分有效[268]。为对抗法伊夫,戈林召来了证人达勒鲁斯,但后者却在法伊夫巧妙的反问下供出了对戈林不利的证言,从而使其受到决定性的打击,达勒鲁斯表示戈林为了实践和平而撒了谎、达勒鲁斯前往柏林总统官邸时看到希特勒的言行像个疯子,以及戈林曾因为毒品中毒而表现出极为兴奋的模样等等[269],法伊夫此举使法庭产生了戈林为和平奔波并非出自其意,而是另有目的的印象[270]。戈林为重整对他有利的情势,声称达勒鲁斯的主张不过是完全主观的印象,完全加以否定[269]。
接着,法伊夫就西里西亚-萨根一处的德国空军战俘营在1944年3月14日有76名英国空军战俘逃脱,后来有50人被盖世太保引渡抓回枪决一事(这个事件后来拍成了美国电影《大逃亡》而颇有知名度)质问戈林,对戈林给予相当有效的打击。接着再以犹太人屠杀问题质问戈林的证人,更是给予其致命的一击:[271]
法伊夫:身为纳粹第二把交椅的你,竟然说对集中营一无所知,对于此事你能够在庭上发誓吗?
戈林:在我不对集中营直接负责后,我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更不晓得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运作。
法伊夫:想想本庭提供的证据吧,有四百万犹太人死于集中营。你是还记得那个被提出的证据吗?
戈林:我曾经在此陈述过,但我认为还未被证实。想起来,这个数字……
法伊夫:就算这数字只有50%的精准度,那也还有200万人,像你这样有权力的高官还对集中营的事完全不知道吗?
戈林:正是如此。那些事情也会对我保密,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即使是元首都不知道事情发展的程度。这也说明,希姆莱对这些事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数字或其他什么情况。
法伊夫:我不问那些事,只问关于400到500万被杀戮的事实。据你所说,除了希姆莱和卡尔滕布伦纳外,德国的权力者都对此浑然不知啰?
戈林:我不是说过,连元首都不知道吗?这就是我的意见。
法伊夫:你该听听希特勒曾发表过的一次言论。希特勒与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曾讲过,犹太人是要将他们加以灭绝好呢,还是把他们赶到集中营?里宾特洛甫也说过这种话。希特勒在1943年4月还曾表示犹太人不是去作奴工,就是把他们枪毙掉。对此你还要坚称说,希特勒与你不知道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吗?
戈林:那法庭纪录有误,要修正……
法伊夫:你只要针对我的问题回答就行了。希特勒和你,都不知道犹太人灭绝政策吗?
戈林:就希特勒来说,我说过,我不相信他了解此事;至于我,我也说过我不知情,连这事大概达到什么程度我都不了解。
法伊夫:也许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知道的,但是您应该知道有这么一项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政策?
戈林:不,我只知道有关于犹太人的移民政策,但不知道灭绝一事。我只知道,这方面的个例里出现了违法行为。
在确认了戈林的回应令全法庭都听到后,法伊夫说了声“非常感谢”,将知道“移民”一事的破绽揪出,该人的质问至此结束[272]。
在这之后,由苏联总检察官罗曼·鲁坚科中将开始进行盘诘。鲁坚科的质问欠缺条理,戈林从容应付之。鲁坚科说道:“请回答我的质问,对这些事明了是你的义务”,戈林则回应:“姑且不论我到底知不知道,但你怎么能硬性的说这是我的义务?”接着鲁坚科问道:“几百万德国人都知道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你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戈林反而对他指出:“但是也有几百万德国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那是一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的说法。[273]”最后,由法国总检察官奥古斯特·尚普捷·德·里布对戈林进行盘诘,不过他也和鲁坚科一样,无法提出有力的问题[274][272]。就这样,检方盘诘阶段结束了[272]。
判决
[编辑]1946年8月31日,审理结束后,被告可于本日做出最后答辩[275]。戈林提出了两个陈述,一个是关于屠杀,一个是关于他本人与战争、人种迫害、征服与榨取等的事情[276][277][278][279]。
到今天为止,我不仅不曾杀人,更不曾发下残虐行为的命令。如果我曾经有过阻止的权限及情报,我绝不允许这类事情的发生。对于我指示海德里希进行犹太人虐杀行动的主张,没有任何的证据。
— 关于屠杀的陈述
我本来就不希望发生战争,为了阻止战争我已透过外交手谈判尽了全力。但战争爆发后,就拿出了全力以确保胜利。鉴于地球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我们,我们终于被拥有巨大优势的敌人征服。对于我自己所做的事不想逃避,但我要极力地否定,我曾经于战争中欲使外国人服从,或者杀戮他们,甚至干过所谓的残虐行为。引导我的唯一动机是我对国民的热爱,以及一心一意要图谋国民的幸福与自由,关于这一点,但愿神与德国国民作为我的证人。
— 关于战争的陈述
1946年9月30日,法庭宣布判决,首席法官劳伦斯宣布如下:[280][281][282]
戈林一案没有任何酌情余地。戈林总是……不,绝多数情况下是仅次于元首的权力者,他既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人,更是侵略战争的统帅。他为强迫奴隶劳动计划的监督者,也是对德国内外的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种进行虐待的主谋。他公开承认了这些罪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里,尽管证词有些出入,但从全面来看,单就其所承认之事实已得以确定其罪。该人罪状极其重大、无人可比。此人根据法庭记录的资料,已没有辩护的余地。在此,法庭认为该人被起诉的四项原因皆为有罪。
戈林听到判决后面无表情[281]。在对所有被告的判决都宣读完后,后者一度各自回到了牢房。下午,被告再各自被带去接受量刑判决,戈林为第一位传唤被告。劳伦斯叫上了“赫尔曼·威廉·戈林”的名字,在即将要宣布判决时,戈林比了个手势,表示他的耳机发不出声,技师上前去维修恢复后,使宣布过程被打断[283]。随后,劳伦斯宣布:“赫尔曼·威廉·戈林。基于你在接受的起诉书上的诉因,国际军事法庭在此宣布你将受绞刑”。听到判决后的戈林慢慢地取下了耳机,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法庭[283][282]。听取被告在接受判决后反应的吉尔伯特,对于戈林的情况有如下描述:“(他)假装保持着镇定,但其中一只手却不停地颤动着。他的眼眶湿润、拼命压抑激动的情绪、不停地喘息著。他要求让自己一个人静静。[283][282]”
自杀
[编辑]
施塔默律师问戈林是否要提出减刑的请求,但受到戈林的拒绝。判决宣布后隔天——10月1日,戈林提出请愿书,要求将绞刑换作枪决,他向吉尔伯特说道:“我是一名军人,一生都以军人的身份度过,我宁愿被其他军人的子弹射倒。因此,能否以敌人组成的行刑枪队来处死我?这绝非一个无理的要求。”然而戈林的请求不被受理[283]。
1946年10月7日,戈林与妻子埃米见了最后一次面,他首先问后者,埃达是否听到判决的事?埃米点了点头。戈林告诉埃米:“我希望埃达的人生不要太过艰难。假如我能够保护你,死亡对我来说也会成了拯救。你想让我更怜悯你吗?”埃米答道:“不,赫尔曼,你在纽伦堡已经为你的战友和国家竭尽了全力,我一直认为你为了德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戈林应道:“真是太抬举我了”,并表示“你可以相信一件事,他们不会绞死我的。[284][285]”
1946年10月15日午后9时30分,含戈林在内的纽伦堡犯人就寝。下午10点44分左右,戈林握了拳、将手臂抬到与脸同高处、做了个像是要遮脸的动作,三分钟后,戈林开始发出类似呼吸困难的声音,监视戈林单人牢房的美军上等兵呼叫他的下士上司:“戈林牢房发生了紧急状况”,在医生抵达现场时,戈林已经断气,他以氰化钾胶囊服毒自杀。在戈林裹上的毛毯和其肚子中间有内藏遗书的信封袋[286],共有给典狱长安德鲁斯、盟军管制委员会、妻子埃米和格雷克牧师的四封遗书[287]。
致典狱长:
打从成为阶下囚那天起,我就一直随身携带着毒药胶囊。我被押送至蒙多夫监狱时,身上共有三粒胶囊,第一粒我留在衣服里,让你们搜身时发现它。第二粒,我更衣时把它藏在衣架下面,穿衣时把它带在身上。不论是在蒙多夫监狱还是在这间小牢房里,我都把这粒药丸藏得很隐密,所以尽管常有严密搜查,还是没有被发现。开庭期间我把它藏在身上或是我的高统靴里。第三粒胶囊如今藏在我小皮箱的护肤霜里。在蒙多夫监狱时,我有两次机会可在必要时用上这粒胶囊,这不能归咎搜查人员,因为要发现胶囊实在不可能,若真的发现也必定是偶然吧。
再启:吉尔伯特医生告诉我,军管委员会已驳回改执行枪决的请愿。
— 致典狱长布尔顿·C·安德鲁斯上校的遗书
致盟军管制委员会:
我本对你们枪毙我不存异议,然而想要将一位德国国家元帅施以绞刑是不可能的!为了德意志着想我不会允许这么做。除此之外,我在道德上没有义务要服从敌人的判决,也因此,我选择和伟大的汉尼拔将军同样的自尽方式。
— 致盟军管制委员会的遗书
我唯一的爱妻,在认真考虑、和上帝诚心祈祷后,为了不给敌人以毒辣的手段处死我的机会,我决定自尽。(中略)在和你挥手道别时就是我人生结束了,从那之后我的心难以置信的平静,认为死亡是最后的解脱。(中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和埃达,我心脏最后一次的跳动将标志着我们伟大和永恒的爱。
— 致妻子埃米的遗书
而给格雷克牧师的信则是非常短,该人为请来给监狱囚犯祈祷的牧师。戈林写道他最终选择自杀、背叛了牧师、请求他的原谅,但“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又不得不这么做。[288]”
安德鲁斯上校赶来查看戈林的遗体后,立即通报了同盟国委员会,接着美英法苏的委员都抵达了现场。突然苏联代表在戈林的尸体脸上打了一记巴掌,其他委员叫道:“这是在干什么?”苏联委员回应:“我认为他在装死,现在确定他真的是死了。[286]”四国的委员商讨对策,一度还想隐瞒自杀的事实,向目击者谎称戈林晕倒了,将尸体弄到绞刑台上行刑,然而因为已有相当数量的人知道戈林自杀了,消息走漏的可能性相当高,这会使得纽伦堡审判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最终决定终止此方案[289]。四国委员同意组成戈林自杀调查委员会,而其他的死刑犯则依照预定行刑[289],安德鲁斯则对外发表戈林自杀、其他犯人继续行刑的消息[289]。后来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戈林的氰化钾入手管道与其遗书的说法属实[290]。
戈林究竟是从何种管道取得毒药一直是个谜,直到2005年2月7日,当时仅19岁、担任监狱看守的美国陆军第1师士兵——赫伯特·李·史蒂福斯(Herbert Lee Stivers)向《洛杉矶时报》供称自己将毒药带入,该人说明:“当时他与一位德国女郎约会,并碰到另外两位德国男人,他们说戈林身体不好,并给了一支钢笔,钢笔里有一颗药,可以给戈林服用”就这样毒药转交到了戈林手中,而这位前美军士兵则因为担忧被严惩而长时间保持沉默[291]。
戈林的自杀对同盟国来说是一大打击。当天各国的新闻版面标题写道:“正义并未胜利,戈林骗到了绞刑执行者”[292]。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导,戈林的自杀在德国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写道:“戈林死时的戏剧性姿态似乎帮助了这些德国人忘记他的罪行。本应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的武器,忽然变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武器。”[292]另外,由于戈林生前曾多次表示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结合不过是战时强迫的利益结合,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使得苏联官员猜测戈林的自杀可能是美国让其在羞耻中挽回名声与荣誉[292]。
戈林以及被处死的10人,共11人的尸体由美军进行拍摄(正面、左侧、右侧、全裸共四张照片)[293]。拍完后,将11具尸体放入木箱中,搬上卡车运至慕尼黑进行火葬。骨灰洒到伊萨尔河的支流孔文茨河(Conwentzbach)中[294][295]。
个人
[编辑]性格
[编辑]戈林的个性十分复杂,在多种场合以不同的面貌示于人前,军史学者马修·库珀(Matthew Cooper)对戈林的评价即诠释了这点:“戈林这个人有如一个谜,他身上有着许多英雄和恶棍的本质,是一位融合诸多矛盾的人物,他既懒散又充满冲劲、既清楚现实又怀着浪漫之情、既残忍又和蔼可亲、既怯懦又勇敢、既文雅又粗鲁、同时有着精明、自负、幽默、冷酷等诸多特质,令人揶揄与厌恶。[296]”
戈林时常因其看似愚蠢乃至狂妄的言行而为人所低估,但实际上戈林也在许多事务上做的很好,美国传记作家何伊特认为戈林是一位组织天才型的政客,他写道:“从最初的冲锋队训练起,凭着他(戈林)公众良好关系的能力网罗了工业界巨头、民航界精英的米尔希与鲁登道夫支持纳粹党、担任希特勒的外交特使、策划德奥合并和控制德国国内的大小经济环节等等……戈林实在太忙了。[297]”作家罗杰·曼维尔也写道:“尽管戈林在表面上看起来奢华无度、古怪荒诞、妄想自大到有时候甚至像个小丑,但实际上他能干又机敏狡猾。他的缺点在二战期间影响深远,也是最终导致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298]”
二次大战之初,戈林还将战争视作中世纪式的“骑士道”对决,他曾试探性地问过战斗机总监加兰特:“如果我要你对从战斗机跳伞降落中的飞行员开枪,你会怎么做?”加兰特道:“报告国家元帅,我认为这是谋杀,我不会执行此命令,也会尽可能阻止这条命令传到下面单位去。”而戈林对这答案非常高兴[299]。另一次,英军著名的空战英雄道格拉斯·巴德被德国空军击落而成了战俘,巴德没有双脚,他请求加兰特能否联络英方送来义肢,而加兰特便向戈林请示,后者高兴地答道:“我们当然会帮助他,加兰特,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299]”
尽管战争期间戈林领导德国空军失败,到了后期只过着吸食毒品、掠夺他国艺术品的奢侈生活,但战争结束后,戒除毒瘾的戈林恢复了战前思路敏捷、精明能干的头脑,在面对盟国检察官质问时,若情况有利于他即坦承以对、博取同情,不利时则闪烁其词[255],往往检察官的问题才刚说出口,戈林就察觉到其意图,借由利用他资料丰富的优势,导致检方的盘问一直毫无进展[265]。英国纽伦堡主审法官诺曼·伯基特即针对戈林的个性与人格做出了评量:“戈林温文尔雅、精明干练、足智多谋,他很快就能看清状况,因而自信心越来越强,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戈林实实在在地主宰了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了不起的是,他在走上证人席之前根本没有公开讲过一句话,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显而易见,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也许具有邪恶本质,却十分出众的枭雄。[269]”
种族观点
[编辑]
戈林被认为是极少数没有对犹太人抱持种族歧视观点的纳粹高级官员,他从小对犹太人就没有什么偏见,甚至私下对第二任妻子埃米承认犹太人比较精明[300]。很多情况中可以看出戈林对犹太人的包容程度,如拯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帮助自己的巴林犹太夫妇和在空军中包庇犹太军官,他的得力助手——赫尔穆特·维尔贝格和米尔希两人皆为二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301],他还亲自帮米尔希伪造血统证明书,成为“正统亚利安人”[302],后来戈林还说过一句话:“在空军中,由我来决定谁是犹太人。[302]”另外,从私人关系来看,戈林长久以来一直否定种族问题的存在,还曾认为犹太人的公司可以资助纳粹,在纳粹取得权力的前期,戈林在反犹主义的会议中还常以“紧急公务”为由开溜[300]。
1935年的《纽伦堡法》通过后,戈林对纳粹政府的种族政策不再装作视而不见了,但尽管如此,当埃米向他要求以其权力从盖世太保处保释某位犹太朋友时,他还是帮了忙,这还让他有过犹太人密友和自由主义份子的好名声[30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戈林并未真正关心犹太人的福利与安全,他更注重的是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戈林曾质疑希特勒的犹太人观点或作法[300]。1938年11月10日,纳粹政府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指挥下,煽动德国人为巴黎的德国大使馆职员被犹太青年刺杀一事报仇,发动了后人称作“水晶之夜”的大规模犹太人迫害行动。戈林闻讯后仓促于12日召开紧急会议检视局势,并在会中大发雷霆,怒斥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被烧毁了,使德国保险公司原本就已高筑的债务又更加攀升,“简直要把人逼疯了!”他还以嘲讽的口吻指责出席会议的海德里希:“我倒希望你杀了两百个犹太人,而不是毁了那么多财产。[303]”后来1939年1月,戈林根据本次会议的结论成立了“犹太移民办事处”,交由海德里希指挥[304]。1941年时,戈林更是下令海德里希解决“犹太人问题”:[305]
为补充1939年1月24日交派给你的任务,亦即根据现况以最佳方式进行移民和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本人兹在此指示你,就组织、财务及物资等事项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势力范围内欧洲犹太人问题……本人更责成你尽速成交一份整体计划,列出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和行动评估。
尽管命令中并未写到使用屠杀的手段、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表示对集中营事务完全不知,但不为纽伦堡的法官所接受,美国检察长杰克逊表示:“戈林带头侵害犹太人,迫使他们逃离德国,流往异乡……亲手签发二十几份迫害犹太人的政令,却从未怀疑过有消灭犹太人的计划。[306]”
至于斯拉夫人,戈林对他们的手段则相当残忍,他曾授权给党卫队领袖希姆莱进行波兰的“德国化”政策,令波兰人被奴役进行强制劳动、强制迁移到屠杀,这些命令文件上都可见到戈林的签名[307]。在发动侵苏战争前,他曾于1941年5月2日向幕僚说道:“战争进入第三年时,我们的军粮必定完全取自于苏联,这场仗才可能继续打得下去。而无疑的,如果我们的所需都来自当地,则数百万人必将饿死。[308]”同年11月,戈林向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半开玩笑地说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了希腊人挨饿而过度担心,别的民族也会受到同样的不幸。在苏联战俘营中,战俘把能吃的都吃了,包括皮靴的鞋底,之后他们开始吃自己人,更要命的是,竟然还把一位德国士兵吃了。今年内,苏联会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死于饥饿。或许这样也好,反正有些国家本来就会饿死一大半的人。如果本来不会饿死的却饿死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显而易见,如果人类注定要饿死的话,你我两个民族会排在最后。[309]”在1941年尾,德军俘虏了约400万的苏联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因希特勒的政策而遭到饿死的命运,剩下的三分之一中也只有约40万人能送到德国后方充作生产军火的奴工,戈林尽管知道德国军火业有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希特勒谋杀数百万俄军战俘时也并未阻止,也因此他被认为在此事上必须负大部分的责任[310]。
奢华的生活
[编辑]
在纳粹高官中,戈林以其生活奢华闻名,不单是生活上的必需品都想用当时最好、最高级、最流行的,他的私人收藏也极多,按照后来盟国的专人鉴定,戈林的收藏品至少值1亿8000万美金、收集的画作多达1300幅[311]。戈林的奢侈态度反应在许多层面,他饲养狮子、在别墅放置大型的火车铁路模型、恢复了魏玛时期禁止的勋章奖励制度,并言道:“魏玛政府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缺乏荣誉与奖章。[312]”戈林还亲自设计了空军的新制服,并规定每位军官都要配有军刀和佩剑。戈林此一作风多少也使空军部分将官跟着腐败了起来[312]。
在与第二任妻子埃米再婚时,戈林举办了一场极为盛大的婚礼,出动了200架飞机、3万官兵列队[313],也邀请了诸多外国宾客,其中的英国大使做了如下评论:“我看他的虚荣与欲望除了皇帝的位子外,没有其他可以给他追求的了……再往上的话就是进断头台了。[314]”美联社记者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 Lochner)也写道:“仿佛是皇帝结婚……戈林是那种人们不能对他发火的人。他的虚荣心很强,他对浮华的嗜好天真得简直让人发笑,但人们也不管它。[315]”
按照米尔希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每个月会给戈林3万马克的特殊津贴,但米尔希也补充这点钱根本不够戈林花一个月[316]。
家庭
[编辑]
在一次大战前期,戈林曾与毛特多夫的一位富家千金玛莉安娜·毛瑟(Marianne Mauser)坠入情网,但她的父亲对于身无财产的戈林并不欣赏,只是鉴于玛莉安娜已为戈林所迷倒而勉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17]。战争结束时,身无分文的戈林被女方父亲所拒,这段恋情因而成了历史[318]。
1920年的一天,正为瑞典航空公司担任职业飞行员的戈林接了瑞典贵族埃里克·冯·罗森伯爵的生意,后来在伯爵城堡过夜时遇见了其夫人的姐姐——卡琳[319]。卡琳比戈林大五岁,她与丈夫尼尔斯还有个八岁大的儿子托马斯,但她并不爱尼尔斯,一心在寻找一位如西格弗里德般的英雄人物,卡琳对年轻的战争英雄戈林一见钟情,而当时的戈林也是生性浪漫、容易动情的人,两人因而坠入情网[319][320]。卡琳因此最终和尼尔斯离婚,后者对卡琳相当地宽容,不仅同意离婚,还给了她一笔钱供其生活[56]。卡琳后来与戈林结识了希特勒,并成了其崇拜者,她曾于一封信中写到对该人的看法:“我想,我们世界上100年来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人了,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321]”在纳粹党于啤酒馆政变失败时,卡琳与戈林逃出德国,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戈林还染上了毒瘾,瘾头发作时还会对卡琳拳打脚踢[322],但她始终对戈林不离不弃。后来戈林重返政治舞台后,卡琳也进入了上层社会,常为戈林张罗宴会。然而卡琳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于1931年10月17日因心脏病去世[323],戈林极为难过,他泪流满面地向卡琳的侄女说他一切的努力与荣耀都只是为了让卡琳过上她为了自己所抛弃的生活[323]。
1932年,戈林结识了年方40岁的埃米·戈林,她是一位出身汉堡的女演员,不仅外表出众,性格天真单纯、不谙政治、也有许多犹太朋友,她已与丈夫离婚。在戈林为卡琳离世而痛苦时,一直是埃米抚慰着他,两人交情也越来越好。但因为戈林终其一生深爱着卡琳(甚至第一件送给埃米的礼物就是卡琳的玉照[324]),戈林一直不再婚,一直到旁人不断劝说此举并不代表对卡琳不忠以及希特勒亲自介入、要戈林给她个名分[325],戈林才于1935年4月10日和埃米结为伉俪[326]。尽管戈林迎娶了埃米,但心中仍一直存在着卡琳的影子。他后来动用公款,修筑了一栋如宫殿般辉煌的邸宅,命名为“卡琳宫”,还将两艘游艇也命名为“卡琳”[327],不过埃米心地宽容大方,并没有对这些事反对[328][327]。1938年6月2日,埃米为戈林生下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的女儿,取名为埃达(Edda),由希特勒担任教父[329]。由于戈林身形肥胖,被人嘲笑性能力有问题,纳粹党内还流传一个笑话,称埃达的父亲其实是戈林的一个副官,埃达的名字也意味着“一切归功于副官”(Es dankt der Adjutant)[327]。
很长时间里,戈林一家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希特勒下令逮捕和杀害戈林一家为止。关于这点戈林一直相信是鲍曼所为,自己仍旧效忠希特勒;而埃米则认为希特勒疯了,戈林必须保护她的女儿,两人还因此大吵一架[330]。战后戈林被捕,埃米也被关到集中营,埃达则被送至孤儿院[327]。埃米在关押了五个月后获释,后于1973年6月10日去世[331]。埃达则一直保持着单身,2018年12月21日去世后安葬于幕尼黑 [332][331]。
荣誉
[编辑]- 军阶
- 1911年5月13日:士官候补生[15]
- 1914年1月20日:少尉[15][333]
- 1916年8月18日:中尉[15][333]
- 1920年6月8日:名誉步兵上尉[15][333]
- 1933年8月30日:名誉步兵上将[333][15]
- 1935年5月21日:航空兵上将[333] [15]
- 1936年4月20日:大将[15][333]
- 1938年2月4日:元帅[15][333]
- 1940年7月19日:国家元帅[15][333]
- 警察阶位
- 纳粹党组织
- 勋奖
| 略章 | 勋奖名 | 授予国家 | 授予时间 | 资料来源 |
|---|---|---|---|---|
| 二级铁十字勋章 | 1914年9月15日 | [333][37] | ||
| 一级铁十字勋章 | 1915年3月22日 | [333][37] | ||
| 骑士佩宝剑二级宰林根雄狮勋章 | 1915年7月8日 | [37] | ||
| 宝剑级霍亨索伦皇家勋章 | 1917年10月20日 | [333][37] | ||
| 骑士十字级卡尔·腓特烈军功勋章 | 1917年10月20日 | [333][37] | ||
| 功勋勋章 | 1918年6月2日 | [333][37] | ||
| 黑色重伤勋章 | 1918年 | [333][37] | ||
| 普鲁士王国飞行员兼观测员奖章 | 1914年11月15日 | [333][37] | ||
| 飞行员奖章 | 1915年10月12日 | [333][37] | ||
| 黄金钻石级飞行员与观测员联合章 | 1935年 | [333][37] | ||
| 钻石级飞行员奖章 | 不明 | [333] | ||
| 前线战士级荣誉十字勋章 | 1934年 | [37] | ||
| 骑士铁十字勋章 | 1939年9月30日 | [333][37] | ||
| 大十字勋章 | 1940年8月19日 | [37] | ||
| 国防军四级长期服役奖章 | 不明 | [37] | ||
| 金、银、铜级纳粹党长期服务奖章 | 不明 | [37] | ||
| 钻石级U型潜艇战斗章 | 1934年 | [333] | ||
| 黄金纳粹党员奖章 | 1933年12月1日 | [333][37] | ||
| 1923年11月9日纪念奖章 | 1933年11月9日 | [333][37] | ||
| 一级、二级但泽十字勋章 | 1939年1月 | [333][37] | ||
| 赫尔曼·戈林航空研究学校纪念勋章 | 1938年1月21日 | [37] | ||
| 1915年版战争奖章 | 不明 | [333][334] | ||
| 大十字章级圣茂里斯及拉匝禄勋章 | 1938年 | [334] | ||
| 天使报喜勋章 | 1940年5月 | [335] | ||
| 大十字章级意大利军事勋章 | 1941年11月27日 | [334] | ||
| 钻石大军官级丹尼布洛勋章 | 1938年8月6日 | [334] | ||
| 大十字级帝国轭箭勋章 | 1938年 | [334] | ||
| 大十字级宝剑勋章 | 1939年2月2日 | [334] | ||
| 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级旭日勋章 | 1943年9月29日 | [334] | ||
| 宝剑一级白玫瑰勋章 | 不明 | [334] | ||
| 一级、二级、三级米歇尔英勇勋章 | 不明 | [334] | ||
| 大十字级战争胜利勋章 | 不明 | [334] |
-
代表戈林的国家元帅旗。
-
德国柏林的联邦国防军空军博物馆展出的戈林国家元帅制服,领口处的勋章即为大十字勋章。
相关条目
[编辑]注解
[编辑]- ^ 戈林的哥哥卡尔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9]。
- ^ 阿尔伯特拒绝加入纳粹党,还在1938年时从事反纳粹运动,后任布拉格斯柯达汽车制造厂外国部长[9]。
- ^ 戈林没有忘记巴林的救助之恩,在纳粹掌权后,戈林一直庇护着身为犹太人的她,并帮助其逃到阿根廷生活。通常犹太人逃到国外后,其国内财产相当于被充公,但在戈林的庇护下,巴林一家的财产仍为其所有[66]。
- ^ 实际上戈林到底有无与墨索里尼见到面有两种说法,根据‘第三帝国の演出者 ヘルマン・ゲーリング伝 上’与《戈林: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两本书的资料显示说有,而‘ナチスの女たち 秘められた爱’一书中又写道未曾见面。
- ^ 在二次大战爆发后,“戈林将集团军”升格为师级单位——第1空降装甲师“赫尔曼·戈林师”,为一支隶属空军的装甲师,以善战闻名,后来戈林忙着掠夺艺术品时,驻于意大利的戈林师也从卡西诺山的修道院盗取大量艺术品给戈林[85]。除了戈林师外,戈林还将空军的地勤人员组成一个个“空军野战师”,这些部队都是高技术层面的地勤人员,进行野战任务非其所长,表现因此相当拙劣[86]。
- ^ 不过乌德特这些话被他的副官马克思·潘德勒(Max Pendele)看到后立刻用抹布擦掉[181],所以戈林被蒙在鼓里,仍不解乌德特自杀的真正原因。尽管戈林在乌德特的葬礼中痛哭,但仍认为后者应为整支德国空军的毁灭负全责[182]。
注脚
[编辑]- ^ 1.0 1.1 1.2 1.3 1.4 1.5 Manvell(2003年),第8页
- ^ Kershaw(2008年),第964页
- ^ オウヴァリー(2012年),第1页
- ^ 4.0 4.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40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0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1-23页
- ^ 8.0 8.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3页
- ^ 9.0 9.1 ゴールデンソーン(2005年),上集,第115页
- ^ 10.0 10.1 10.2 10.3 Miller(2006年),第444页
- ^ 11.0 11.1 11.2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33页
- ^ 12.0 12.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7页
- ^ 13.0 13.1 13.2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6页
- ^ 学研(2007年),第138页
- ^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Miller(2006年),第42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4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5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88页
- ^ 19.0 19.1 19.2 Manvell(2003年),第14页
- ^ 20.0 20.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30页
- ^ 21.0 21.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20页
- ^ Hoyt(1995年),第9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8页
- ^ Hoyt(1995年),第10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89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29页
- ^ 27.0 27.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36页
- ^ キレン(1973年),第4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39页
- ^ 30.0 30.1 Miller(2006年),第424页
- ^ 31.0 31.1 31.2 31.3 Manvell(2003年),第1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4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47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50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51页
- ^ 36.0 36.1 学研(2007年),第136页
- ^ 37.00 37.01 37.02 37.03 37.04 37.05 37.06 37.07 37.08 37.09 37.10 37.11 37.12 37.13 37.14 37.15 37.16 37.17 37.18 37.19 37.20 Miller(2006年),第442页
- ^ Manvell(2003年),第17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57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6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64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44页
- ^ 43.0 43.1 キレン(1973年),第5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67-6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68页
- ^ Manvell(2003年),第20页
- ^ ドラリュ(2000年),第5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75页
- ^ Manvell(2003年),第23页
- ^ キレン(1973年),第60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76页
- ^ 52.0 52.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77页
- ^ ジークムント(2009年),第39页
- ^ ジークムント(2009年),第4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85页
- ^ 56.0 56.1 Manvell(2003年),第28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92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94页
- ^ Manvell(2003年),第30页
- ^ 60.0 60.1 60.2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9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02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98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99页
- ^ Manvell(2003年),第36页
- ^ Manvell(2003年),第3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50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13页
- ^ Manvell(2003年),第40页
- ^ ジークムント(2009年),第47页
- ^ ジークムント(2009年),第5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26页
- ^ Manvell(2003年),第42页
- ^ 森瀬缭、司史生(2008年),第41页
- ^ ドラリュ(2000年),第57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94页
- ^ ドラリュ(2000年),第58页
- ^ 77.0 77.1 Miller(2006年),第429页
- ^ ドラリュ(1968年),第59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47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69-170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202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82页
- ^ ウィリアムソン(1995年),第46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8页
- ^ Flames Of War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22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198页
- ^ Shirer(1960年),第193页
- ^ The Avalon Project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17页
- ^ Manvell(2003年),第69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233页
- ^ 94.0 94.1 学研(2001年),第114页
- ^ ドラリュ(1968年),第81页
- ^ グレーバー(2000年),第76页
- ^ 大野英二(2001年),第90页
- ^ Evans(2005年),第54页
- ^ ヘーネ(1981年),第98页
- ^ Jörgensen(2004年),第191-194页
- ^ Irving(2002年),第168页
- ^ Irving(2002年),第171页
- ^ フライ(1994年),第29页
- ^ ヘーネ(1981年),第104页
- ^ Persico(1996年),第215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36页
- ^ Der Spiegel(1984年),第122页
- ^ Irving(2002年),第195-196页
- ^ ヘーネ(1981年),第130页
- ^ 森瀬缭、司史生(2008年),第19页
- ^ ヴィストリヒ(2002年),第185页
- ^ ヘーネ(1981年),第12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39页
- ^ Persico(1996年),第216页
- ^ 115.0 115.1 Miller(2006年),第430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99页
- ^ Manvell(2003年),第78页
- ^ 118.0 118.1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21页
- ^ Irving(2002年),第26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上集,第208页
- ^ Manvell(2003年),第86页
- ^ 122.0 122.1 Mitcham(2008年),第84页
- ^ 123.0 123.1 123.2 Mitcham(2008年),第85页
- ^ Murray(2000年),第4页
- ^ Mitcham(2008年),第87页
- ^ Mitcham(2008年),第88页
- ^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Mitcham(2008年),第89页
- ^ 128.0 128.1 Mitcham(2008年),第93页
- ^ Murray(2000年),第11页
- ^ 130.0 130.1 Mitcham(2008年),第90页
- ^ Murray(2000年),第12页
- ^ 132.0 132.1 Murray(2000年),第5页
- ^ Millman(1998年),第125页
- ^ オウヴァリー(2000年),第58页
- ^ 成瀬治、山田欣吾、木村靖二(1997年),第236页
- ^ 136.0 136.1 成瀬治、山田欣吾、木村靖二(1997年),第237页
- ^ 成瀬治、山田欣吾、木村靖二(1997年),第264页
- ^ Manvell(2011年),第98页
- ^ Hoyt(1995年),第117页
- ^ Irving(2002年),第282页
- ^ Irving(2002年),第284页
- ^ Höhne(1984年),第96-98页
- ^ Kershaw(2000年),第96、112页
- ^ Irving(2002年),第287页
- ^ Irving(2002年),第292页
- ^ Irving(2002年),第290页
- ^ Irving(2002年),第291页
- ^ Irving(2002年),第251页
- ^ Irving(2002年),第250页
- ^ Evan(2005年),第646-652页
- ^ 151.0 151.1 Hoyt(1995年),第120-122页
- ^ Hoyt(1995年),第128页
- ^ Manvell(2003年),第121页
- ^ Manvell(2003年),第124页
- ^ Manvell(2003年),第126页
- ^ Manvell(2003年),第131-135页
- ^ Manvell(2003年),第136页
- ^ Irving(2002年),第396页
- ^ Irving(2002年),第399页
- ^ Irving(2002年),第404页
- ^ Shirer(1960年),第721、723页
- ^ 162.0 162.1 162.2 162.3 Mitcham(2007年),第92页
- ^ Mitcham(2007年),第93页
- ^ 164.0 164.1 Mitcham(2007年),第94页
- ^ 165.0 165.1 165.2 Mitcham(2007年),第96-97页
- ^ Hoyt(1995年),第167页
- ^ Hoyt(1995年),第16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81-82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82页
- ^ Evans(2008年),第144页
- ^ Evans(2008年),第145页
- ^ ww2gravestone
- ^ Hoyt(1995年),第175、181页
- ^ 174.0 174.1 Levine(1992年),第17页
- ^ 175.0 175.1 O'Connell(2011年),第10-11页
- ^ 176.0 176.1 Irving(2002年),第465页
- ^ Hoyt(1995年),第195页
- ^ Hoyt(1995年),第196页
- ^ Manvell(2003年),第149-150页
- ^ Hoyt(1995年),第204-205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11页
- ^ 182.0 182.1 Mitcham(2007年),第156页
- ^ WDR Stichtag
- ^ Evans(2008年),第404–405页
- ^ Evans(2008年),第412-413页
- ^ Speer(1971年),第329页
- ^ Evans(2008年),第421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4-155页
- ^ Evans(2008年),第438、441页
- ^ Evans(2008年),第461页
- ^ Evans(2008年),第447页
- ^ Mitcham(2007年),第235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2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5-156、161页
- ^ Manvell(2011年),第296、297、299页
- ^ Evans(2008年),第510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7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7、160页
- ^ Manvell(2003年),第161-162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45-14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45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145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64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47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48页
- ^ 206.0 206.1 マーザー(1979年),第56页
- ^ 207.0 207.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49页
- ^ 208.0 208.1 208.2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50页
- ^ 209.0 209.1 マーザー(1979年),第57页
- ^ 210.0 210.1 Manvell(2003年),第164页
- ^ 211.0 211.1 211.2 211.3 Irving(2002年),第14-15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91页
- ^ 213.0 213.1 Manvell(2003年),第167页
- ^ 214.0 214.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52页
- ^ 215.0 215.1 215.2 マーザー(1979年),第5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53页
- ^ クノップ(2001年),上集,第146页
- ^ 218.0 218.1 218.2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54页
- ^ 219.0 219.1 219.2 Persico(1996年),第33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59页
- ^ Irving(2002年),第692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58-159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59-60、7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59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76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62-16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61页
- ^ 228.0 228.1 Persico(1996年),第69页
- ^ Manvell(2003年),第172页
- ^ 230.0 230.1 Manvell(2003年),第174页
- ^ 231.0 231.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67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105页
- ^ Persico(1996年),第11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66页
- ^ Persico(1996年),第123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112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126页
- ^ Persico(1996年),第169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71-172页
- ^ Manvell(2003年),第175页
- ^ Persico(1996年),第178页
- ^ Persico(1996年),第179页
- ^ Persico(1996年),第195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72页
- ^ 245.0 245.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73页
- ^ 246.0 246.1 Persico(1996年),第239-240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76页
- ^ Persico(1996年),第256、298-299页
- ^ Manvell(2003年),第176-177页
- ^ 250.0 250.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78页
- ^ Persico(1996年),第315页
- ^ Persico(1996年),第316页
- ^ 253.0 253.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79页
- ^ Persico(1996年),第317页
- ^ 255.0 255.1 255.2 Manvell(2003年),第177页
- ^ Manvell(2003年),第178页
- ^ Persico(1996年),第318页
- ^ Persico(1996年),第321页
- ^ Persico(1996年),第322页
- ^ 260.0 260.1 260.2 260.3 Persico(1996年),第323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2页
- ^ Persico(1996年),第325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180-181页
- ^ Persico(1996年),第328页
- ^ 265.0 265.1 265.2 Manvell(2003年),第180页
- ^ 266.0 266.1 Persico(1996年),第329-330页
- ^ 267.0 267.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1页
- ^ Persico(1996年),第334页
- ^ 269.0 269.1 269.2 Manvell(2003年),第181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9页
- ^ Manvell(2003年),第181-183页
- ^ 272.0 272.1 272.2 Persico(1996年),第335页
- ^ Manvell(2003年),第183-184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1-182页
- ^ Persico(1996年),第430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35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4页
- ^ Persico(1996年),第432页
- ^ Manvell(2003年),第185-186页
- ^ マーザー(1979年),第190-191页
- ^ 281.0 281.1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7页
- ^ 282.0 282.1 282.2 Manvell(2003年),第186页
- ^ 283.0 283.1 283.2 283.3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88页
- ^ モズレー(1977年),下集,第190-191页
- ^ ジークムント(2009年),第92-93页
- ^ 286.0 286.1 Persico(1996年),第483页
- ^ Persico(1996年),第477-478页
- ^ Persico(1996年),第478页
- ^ 289.0 289.1 289.2 Persico(1996年),第484页
- ^ Persico(1996年),第492页
- ^ BBC News
- ^ 292.0 292.1 292.2 Persico(1996年),第491页
- ^ Persico(1996年),第487页
- ^ Persico(1996年),第489页
- ^ 阿部良男(2001年),第662页
- ^ Mitcham(2007年),第1页
- ^ Hoyt(1995年),第298页
- ^ Manvell(2003年),第94页
- ^ 299.0 299.1 Fraschka(1997年),第39-40页
- ^ 300.0 300.1 300.2 300.3 Hoyt(1995年),第118-119页
- ^ Corum(1997年),第127页
- ^ 302.0 302.1 Mitcham(2007年),第8-9页
- ^ Manvell(2003年),第114页
- ^ Manvell(2003年),第116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1页
- ^ Manvell(2003年),第184页
- ^ Manvell(2003年),第140页
- ^ Manvell(2003年),第148页
- ^ Manvell(2003年),第151-152页
- ^ Hoyt(1995年),第213页
- ^ Hoyt(1995年),第168-169页
- ^ 312.0 312.1 Irving(2002年),第222页
- ^ Irving(2002年),第223页
- ^ Irving(2002年),第242页
- ^ Irving(2002年),第223、225页
- ^ Irving(2002年),第704页
- ^ Hoyt(1995年),第21页
- ^ Hoyt(1995年),第34页
- ^ 319.0 319.1 Hoyt(1995年),第38-39页
- ^ Manvell(2003年),第26页
- ^ Irving(2002年),第90页
- ^ Irving(2002年),第110页
- ^ 323.0 323.1 Persico(1996年),第342页
- ^ Persico(1996年),第343页
- ^ Irving(2002年),第219-220页
- ^ Manvell(2003年),第71、86页
- ^ 327.0 327.1 327.2 327.3 Persico(1996年),第344页
- ^ Irving(2002年),第142页
- ^ Irving(2002年),第333页
- ^ Persico(1996年),第345页
- ^ 331.0 331.1 Lebert(2000年),第187页
- ^ Daily Mail Reporter
- ^ 333.00 333.01 333.02 333.03 333.04 333.05 333.06 333.07 333.08 333.09 333.10 333.11 333.12 333.13 333.14 333.15 333.16 333.17 333.18 333.19 333.20 333.21 333.22 333.23 333.24 333.25 Dixon(2009年),第17页
- ^ 334.00 334.01 334.02 334.03 334.04 334.05 334.06 334.07 334.08 334.09 Miller(2006年),第443页
- ^ Manvell(2003年),第126-127页
参考资料
[编辑]- 出版品
- (日语)阿部良男, 『ヒトラー全記録 : 1889-1945 20645日の軌跡』, 柏书房, 2001, ISBN 978-4760120581
- (日语)ヴィストリヒ, ロベルト, 『ナチス時代 ドイツ人名事典』, 东洋书林, 2002, ISBN 978-4887215733
- (日语)ヘーネ, ハインツ, 『SSの歴史 髑髏の結社』, フジ出版社, 1981, ISBN 978-4892260506
- (日语)ウィリアムソン, ゴードン, 『鉄十字の騎士 騎士十字章の栄誉を担った勇者たち』, 大日本絵画, 1995, ISBN 978-4499226523
- (日语)金森诚也, 『ゲーリング言行録 ナチ空軍元帥おおいに語る』, 荒地出版社, 2002, ISBN 978-4752101284
- (日语)キレン, ジョン, 『鉄十字の翼 ドイツ空軍 1914-1945』, 早川书房, 1973, ASIN B000J9JT8Q
- (日语)クノップ, グイド, 『ヒトラーの共犯者 上 12人の側近たち』, 原书房, 2001, ISBN 978-4562034178
- (日语)ゴールデンソーン, レオン, 『ニュルンベルク・インタビュー 上』, 河出书房新社, 2005, ISBN 978-4309224404
- (日语)ジークムント, アンナ・マリア, 『ナチスの女たち 秘められた愛』, 东洋书林, 2009, ISBN 978-4887217614
- (日语)ドラリュ, ジャック, 『ゲシュタポ・狂気の歴史―ナチスにおける人間の研究』, サイマル出版会, 1968, ASIN B000JA4KQQ
- (日语)ドラリュ, ジャック, 『ゲシュタポ・狂気の歴史』, 讲谈社学术文库, 2000, ISBN 978-4061594333
- (日语)グレーバー, ゲリー・S・, 『ナチス親衛隊』, 东洋书林, 2000, ISBN 978-4887214132
- (日语)フライ, ノルベルト, 『総統国家 ナチスの支配 1933―1945年』, 岩波书店, 1994, ISBN 978-4000012409
- (日语)ヘーネ, Heinz, 『SSの歴史 髑髏の結社』, フジ出版社, 1981, ISBN 978-4892260506
- (日语)ヘーネ, Heinz, 『SSの歴史 髑髏の結社 上』, 讲谈社学术文库, 2001, ISBN 978-4061594937
- (日语)ヘーネ, ハインツ, 『SSの歴史 髑髏の結社 下』, 讲谈社学术文库, 2001, ISBN 978-4061594944
- (日语)マーザー, ウェルナー, 『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 ナチス戦犯はいかにして裁かれたか』, TBSブリタニカ, 1979
- (日语)モズレー, レナード, 『第三帝国の演出者 ヘルマン・ゲーリング伝 上』, 早川书房, 1977, ISBN 978-4152051349
- (日语)モズレー, レナード, 『第三帝国の演出者 ヘルマン・ゲーリング伝 下』, 早川书房, 1977, ISBN 978-4152051332
- (日语)森瀬缭、司史生, 『図解第三帝国』, 新纪元社, 2008, ISBN 978-4775305515
- (日语)学研, 『図説ドイツ空軍全史』, 历史群像 欧州戦史シリーズ, 学研, 2007, ISBN 978-4056047899
- (日语)学研, 『武装SS全史 (1) 』, 历史群像 欧州戦史シリーズ, 学研, 2001, ISBN 978-4056026429
- (日语)时事通信社, 『ニュルンベルグ裁判記録』, 时事通信社, 1947
- (日语)大野英二, 『ナチ親衛隊知識人の肖像』, 未来社, 2001, ISBN 978-4624111823
- (日语)成瀬治、山田欣吾、木村靖二, 『ドイツ史〈3〉1890年~現在』, 山川出版社, 1997, ISBN 978-4634461406
- (日语)オウヴァリー, リチャード, 『ヒトラーと第三帝国』, 河出书房新社, 2000, ISBN 978-4309611853
- (德文)Beckh, Joachim, Blitz & Anker, Band 2: Informationstechnik, Geschichte & Hintergründe, Books on Demand, 2005, ISBN 978-3833429972
- (英文)Boog, Horst,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VII: The Strategic Air War in Europe and the War in the West and East Asia, 1943-194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198228899
- (英文)Corum, James, The Luftwaffe: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978-0-7006-0836-2
- (英文)Dixon, Jeremy, Luftwaffe Generals The Knight's Cross Holders 1939-1945,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2009, ISBN 978-0764332432
- (德文)Der Spiegel, Der Spiegel 第26期, 1984
- (英文)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New York: Penguin, 2005, ISBN 978-0-14-303790-3
- (捷克文)Höhne, Heinz, SS - Elita ve stínu smrti, Grada Publishing, 2012, ISBN 978-8024739724
- (英文)Hooton, Edward, Phoenix Triumphant: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Luftwaffe, Garden City: Arms & Armour, 1999, ISBN 1-85409-181-6
- (英文)Jörgensen, Christer, Hitler's Espionage Machine: Germ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Oper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History Press Limited, 2004, ISBN 978-1862272446
- (英文)Kershaw, Ian, Hitler: A Biograph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ISBN 978-0-393-06757-6
- (法文)Kershaw, Ian, Hitler : 1936-1945 : Némésis, Paris: Flammarion, 2000, ISBN 978-2-082-12529-1
- (英文)Kilduff, Peter, Hermann Göring - Fighter Ace, Grub Street Publishing, 2010, ISBN 978-1906502669
- (德文)Lebert, Stephan, Denn Du trägst meinen Namen – Das schwere Erbe der prominenten Nazi-Kinder, Munich: Karl Blessing Verlag, 2000, ISBN 978-3896671059
- (英文)Levine, Alan J., The Strategic Bombing of Germany: 1940-1945,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2, ISBN 978-0275943196
- (英文)Millman, Brock, Ill-Made Alliance: Anglo-Turkish Relations, 1934-1940, McGill-Queen's Press, 1998, ISBN 978-0773516038
- (英文)Mitcham, Samuel W., The Rise of the Wehrmach: The German Armed Forces and World War II, ABC-CLIO, 2008, ISBN 978-0275996413
- (英文)Mitcham, Samuel W., Eagles of the Third Reich: Men of the Luftwaffe in World War II, Stackpole Books, 2007, ISBN 978-0811734059
- (英文)Miller, Michael D., Leaders of the SS & German Police, Volume I, Bender Publishing, 2006, ISBN 932-9700373
- (英文)Murray, ウィリアムソン, 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 Air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1-58566-010-8
- (英文)O'Connell, John F., Submarin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the 20th Century: Part Two (1939 - 1945), Bloomington: iUniverse, 2011, ISBN 978-1462042579
- (英文)Russell, Francis, The secret war, New York: Time-Life Books, 1998, ISBN 978-0783557007
- (英文)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0, ISBN 978-0671624200
- (英文)Speer, Albert, Inside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Avon, 1971 [1969], ISBN 978-0-380-00071-5
- (中文)Fraschka, Günter, 《帝國騎士 : 27位騎士十字勳章得主》, 台北市: 麦田出版, 1997, ISBN 957-708-495-8
- (中文)Hoyt, Edwin P., 《納粹飛鷹:戈林和德國空軍》, 台北市: 麦田出版, 1995 [1994], ISBN 957-708-324-2
- (中文)Persico, Joseph E., 《紐倫堡大審》, 台北市: 麦田出版, 1996 [1994], ISBN 957-708-439-7
- (中文)Manvell, Roger, 《戈林:納粹德國空軍總司令》, 台北市: 星光出版社, 2003 [1962], ISBN 957-677-535-3
- 线上资料
- (英文)Guard 'gave Goering suicide pill', BBC News, [2013-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21)
- (英文)Nazi christening gown given to Goering's daughter by Hitler to be auctioned, Baenebooks, [2013-03-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6)
- (英文)Irving, David, Göring. A Biography (PDF), Parforce UK Ltd, 2002 [2012-03-2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7-13)
- (英文)Hermann Wilhelm Göring, The Aerodrome, [2013-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21)
- (英文)Nuremberg Trial Proceedings, Volume 9,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2012-03-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4-15)
- (英文)Goering, Peter, ww2gravestone.com, [2012-03-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4)
- (英文)Luftwaffe Field Divisions, flamesofwar.com, [2012-03-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8-01)
- (德文)"Des Teufels General". Vor 65 Jahren: Generaloberst Ernst Udet erschießt sich, WDR Stichtag, [2013-0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1-26)
- (德文)Höhne, Heinz, »Entehrend für die ganze Armee« - DER SPIEGEL, spiegel, 1984-02-06 [2023-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7-19)
外部链接
[编辑]- 赫尔曼·戈林(德国国家图书馆目录相关文献)
- (德文)1943年1月30日,戈林於納粹黨上台執政十週年紀念日發表關於「史達林格勒」的弔唁, historisches-tonarchiv.de, [2013-07-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03)
- (德文)德國歷史博物館中關於戈林的藝術收藏紀錄, dhm.de, [2013-07-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8)
| 军职 | ||
|---|---|---|
| 前任者: 埃里希·维兰 |
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 1917–1918 |
继任者: 赫尔曼·弗罗姆赫茨 |
| 前任者: 威廉·赖因哈德 |
第1战斗机联队队长 1918 |
继任者: 埃里希·冯·维德尔 |
| 前任者: 埃里希·冯·维德尔 |
第1战斗机联队队长 1918 |
本单位解散 |
| 新头衔 本单位创建
|
德国空军总司令 1935–1945 |
继任者: 罗伯特·冯·格莱姆骑士 |
| 官衔 | ||
| 前任者: 汉斯·乌尔里希·克林奇 |
冲锋队总指挥 1923 |
空缺 下一位持有相同头衔者: 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
|
| 前任者: 保罗·勒伯 |
德国国会议长 1932–1945 |
国会废除 |
| 前任者: 弗朗茨·冯·帕彭 |
普鲁士总理 1933–1945 |
普鲁士邦废除 |
| 前任者: 阿道夫·希特勒 |
普鲁士邦帝国总督 1935–1945 |
普鲁士邦废除 |
| 前任者: 亚尔马·沙赫特 |
经济部长 1937–1938 |
继任者: 瓦尔特·冯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