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
|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 |
|---|---|
 1918年的韦伯 | |
| 出生 | 1864年4月21日 |
| 逝世 | 1920年6月14日(56岁) |
| 国籍 | 德国 |
| 母校 | 腓特烈·威廉大学 哥廷根大学 海德堡大学 |
| 职业 |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 |
| 机构 | 腓特烈·威廉大学 弗莱堡大学 海德堡大学 维也纳大学 慕尼黑大学 |
| 知名作品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1]《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
| 信仰 | 基督教[2] |
| 配偶 | 玛丽安妮·韦伯 |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德语: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小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虽然韦伯本人并不用社会学家这一头衔来定义自己,但他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一起被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
比起推崇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3]和追求实证主义的杜尔凯姆[4],韦伯更强调主观意志在社会科学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研究需要以主观构建的理想类型为框架,[5]并可以以人们的主观信念为主题。韦伯因此就宗教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大命题。这在其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第一,韦伯描述了新教中的禁欲思想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且提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距的重要原因。第二,韦伯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加深,西方社会在朝着世俗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韦伯是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6]他将社会组织中的权威分成三类: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韦伯认为在现代化与理性化的进程之中,传统型权威正逐步让步于法理型权威。他还将国家政体定义为一个“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社会实体。[7]这个定义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韦伯最初在腓特烈·威廉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颇具影响,曾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德国在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团,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
生涯
[编辑]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普鲁士王国萨克森省的埃尔福特市,[5]后随家人于1869年迁至柏林。[8]韦伯在家中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一,[9]其父亲老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律师、[5]公务员和政治家,是普鲁士议会以及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9]韦伯的母亲海伦妮·韦伯出身富裕,[9]祖上有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移民。[5]在生活方面,老马克斯追求享受,对宗教与慈善事业不闻不问,而海伦妮则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教徒,[9]追求禁欲主义,[5]在道德方面持有许多绝对主义的观点。[10]父母两人不同的处世之道对小马克斯·韦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韦伯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与学术氛围,许多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其中包括哲学家威廉·狄尔泰以及法官与法学家莱文·戈尔德施密特。[8]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877年圣诞节期间,年仅十三岁的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大迁徙的历史》。[11]
少年时期的韦伯对学校老师的授课提不起兴趣,而老师也觉得韦伯不懂尊重他人。然而,韦伯在学习方面表现依然突出。韦伯十四岁时,其信件便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古典著作,在他进入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文学家歌德以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8]

1882年,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念书[12]。如同他父亲,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意志帝国陆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洪堡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服短期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12]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13]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年代后期韦伯继续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律博士学位[12]。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13],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14],其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画,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14]。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1893年韦伯与远亲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后者后来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15]。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3]。1896年韦伯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13]。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16]。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13]。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著在年底和妻子前往义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宋巴特[17]创办《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期刊[18][19],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20],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21]。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著私人学者的身分。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18]。在1912年,韦伯试著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2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韦伯在海德堡的一间陆军医院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院长[23][18]。在1915年和1916年他出任一个政府的委员会,试图保持德国在战后于比利时和波兰的主权。韦伯个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当时德国帝国扩张的看法则随著战局的每况愈下而改变[23][22][24]。韦伯在1918年成为海德堡的劳工和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918年韦伯成为德国休战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德国代表团前往凡尔赛会议,并且也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18]。当时韦伯支持在宪法中加入授权紧急戒严的第48号条款[25],这个条款后来由于被阿道夫·希特勒用于建立独裁统治而恶名昭彰。韦伯对于德国政治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
韦伯在这时开始重掌教职,首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接著是在1919年于慕尼黑大学[18]。在慕尼黑大学,他建立了第一所德国大学的社会学学系,但最后从没有亲自担任社会学的教职。由于德国右派在1919年和1920年掀起的动荡,韦伯离开了政治界。当时许多慕尼黑大学的同僚和学生批评他在1918年和1919年的德国革命中的亲左派态度和演讲,一些右派的学生还在他住家前抗议[22]。韦伯在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死于慕尼黑[18]。
学术成就
[编辑]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杜尔凯姆)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26],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26][27]。涂尔干遵循著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宋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28],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28],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韦伯将其分类为传统行为、感情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和附带行为[29]),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喀尔文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确实是天选之人。[30]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31]。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暗示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宗教社会学
[编辑]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探索。他对于其他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画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32]。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33]。
他的目标是为了找出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不过与当时许多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韦伯最初并没有打算衡量和评断东西方两者的优劣;他希望专注于研究并解释西方文化特殊之处[33]。在他的研究分析里,韦伯指出喀尔文主义(或者更广泛的——基督教)宗教理想的影响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这并非促成发展唯一的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还包括了理性主义对于科学的追求、加上数学的科学统计、法律学、以及对于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统化、和经济上的企业[33]。最后,依据韦伯的看法,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只不过是探索一个阶段的变革,亦即那些让西方文明突出于其他文明之外的重要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编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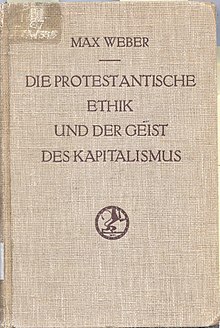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最知名的著作[20]。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30]。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34],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35]。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35]。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30]。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36]。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了。
《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
[编辑]《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37]。
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以世袭制度相传的帝国[37]。如同在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了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亲戚关系的紧密连结造成的,而这种连结则是出于宗教信仰里的祖传观念。另外,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著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也因此,中国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如同欧洲城市一般的独特社会阶级[38]。
较早的国家统一以及中央官僚制度的建立,则意味著中国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僚的贪污小费和税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有50%的税入都流入了他们的口袋。帝国的政府则依赖于这些官僚的服务,而非如同欧洲一般依赖于骑士的军事服务[38]。
韦伯指出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从没有试著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教导人们要顺著这个世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39]。
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伟大神祇的敬仰只是政府的事务,而对于祖先的敬仰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除此之外许许多多民间的信仰都被容忍。儒教也容忍巫术和神秘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作为帮助控制群众的有用工具;但若是他们威胁到既有的秩序,儒教便会谴责其为异端并毫不犹豫的加以镇压(如同对于佛教的压迫)。在这里儒教指的是作为一种国教,而道教则是民间的信仰[40] 。
韦伯主张,虽然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法抵销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
- 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择。
- 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困难
- 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
- 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37]。
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著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韦伯主张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41]。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编辑]《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42]。
印度的社会体制是由种姓制度的概念所形塑,直接连结了宗教思想与社会上的阶级分隔的关系。韦伯描述这种种姓制度是由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战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劳工)所组成。接著他指出种姓制度在印度的散布是因为历史上的征服侵略所造成,某些部落遭到了边缘化、种族制度也因此越来越根深蒂固[42]。
韦伯特别专注于对婆罗门阶级的研究,并分析他们为何能够占据印度社会的最高阶级位置长达数个世纪。在研究了佛法概念的影响后,韦伯总结认为印度社会的道德观多元倾向,与儒教和基督教普世而统一的道德观不相同。如同中国一样,他注意到种姓制度也妨碍了印度都市独特阶级的发展[43]。
紧接著,韦伯分析了印度的宗教思想,包括了禁欲主义和印度的世界观、婆罗门的正统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崛起和衰退、以及古鲁(印度教祭司)的发展。韦伯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日常的世俗活动有没有任何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它又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韦伯注意到印度教里所强调的永恒不变的世界秩序,是由永不停止的轮回概念和对现世世界的敌意所构成,他发现这种由宗教支持的传统种姓制度最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种姓制度的“精神”对于当地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极大的阻挠作用[43]。
在研究的总结里,韦伯将他对于印度社会学和宗教的研究与之前对中国的研究综合起来。他注意到这些宗教都将人类生命的意义解释为超脱世俗的或是神秘性的经验,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通常倾向于厌恶政治,而社会架构往往被区分为受过教育与否的两种阶级,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作为先知或智者的榜样,而未受教育的大众则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庸俗里并且相信迷信的民间巫术。在亚洲社会,如同基督教弥赛亚一般、能够不分受过教育与否皆给予救赎和指引的救世主并不存在。韦伯主张,正是因为弥赛亚救世主起源于近东国家,使得他们与亚洲大陆的主要宗教产生差异,西方国家也因此免于陷入中国和印度的道路。韦伯在他下一本著作《古犹太教》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论点[44]。
《古犹太教》
[编辑]《古犹太教》是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第四本著作,韦伯试著解释“各种情况的结合”导致了早期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45]。尤其是将西方基督教的世俗禁欲主义与印度发展出的神秘冥思信仰相对照时,这种差异显得特别明显[45]。韦伯注意到一些基督教的观点带有征服和改变世界的理想,而不加以逃避之[45]。这种基督教的基本特征(当与远东的宗教相对照时)则是源于古代犹太人的先知[46]。当韦伯述及他研究古犹太教的原因时,他写道“任何在现代欧洲文明传统下成长的人都会自然的以一连串的假设来解决遇到的历史问题,这对他而言是不可避免而且也相当合理的。这些问题将可以找出在各种情况的结合下,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普遍的独特文化涵义。[45]”
“对于犹太人而言……世界的社会秩序已经发展至与当初先知对于未来的诺言相反的情况了,但他们仍认为未来这种情况会被改变、犹太人也会再次崛起。在犹太人看来来,世界既不是永恒的也非一成不变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世界表现出的架构就如同一个人行为的结果,除了所有犹太人之外、加上上帝对他们的反应而形塑而成的。也因此世界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被设计用以实现上帝指定的秩序的…除此之外它是存在于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宗教伦理的社会上;它不受神秘巫术以及其他所有非理性寻求救赎的行为的影响;它与那些亚洲宗教提出的救赎途径完全处于不同的世界。更广泛的说这种道德观在今天依然是中东和欧洲的基本道德观。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便是出自这个原因。…也因此,在思考到犹太人当初发展的历史时,我们便来到了西方和中东整个文化发展的分水岭[46]。”
韦伯分析了中东贝都因人、城邦、牧人和农夫、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兴起和衰落。联合王国的时期就仿佛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将出埃及记以来的联邦时期与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殖民时期一分为二。这种时期的区分和宗教的历史有极大关系,由于犹太教的基本教义是在以色列联邦时期形成的,它们在联合王朝衰败后成为了先知概念的基础,并在后来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7]。
韦伯讨论了早期以色列的联邦架构、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独特关系、外国宗教的影响、宗教狂热的形式、以及犹太教祭司们对抗宗教狂热和偶像崇拜的斗争。他接著描述了王国的分裂、圣经的先知们在社会方面的态度、蛊惑人心的政客、宗教迷信和政治,以及先知们的道德观。韦伯注意到犹太教不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始祖,同时也是现代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社会学家赖因哈德·本迪克斯概述《古犹太教》一书道:“在上帝的凝视下,努力免于巫术和神秘迷信、献身于法律的研究、谨慎选择作出正确的事情,以此期盼未来能够更好,先知们设立了这样一个将人的日常生活置于服从上帝指示的道德法则下的宗教。透过这样的教义,古犹太教促成了道德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的诞生。[48]”
政治和政府社会学
[编辑]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志》(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49],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也因此一个政治家不能被视为是一个“真正道德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如同山上宝训里所述的会将脸颊转过来让人掴耳光。遵从那样的道德的人应该被归属于圣人,只有圣人才会这样做。而现实的政治界是没有允许圣人参与的空间的,一个政治家应该采纳的伦理是道德与政治目标的权衡(Proportion)、以及负责任的伦理(Responsibility),并且必须对他的职业拥有强烈的热情(Passion)、同时还必须学会将自己的情绪好恶与实际目标区隔开来(Distance)[50]。
韦伯并且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权威(家族和宗教)、传统型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法理型权威(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51]。韦伯主张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52]。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常规的”权威形式,也就是传统或者官僚型支配。同样的,他也注意到在纯粹的传统型支配里,对于支配者的抵抗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传统的革命”。因此韦伯也暗示了社会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利用官僚的架构制度[53]。尽管韦伯庞杂的著作中暗示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他自己十分小心避免进化论与目的论的逻辑。然而由于韦伯最早的英译来自结构功能派的塔尔科特·帕森斯,使得他的理论时常被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部分。
韦伯在社会的官僚化上的批判研究也相当为人所知,研究一个正式的社会体制如何以理性的方式套用某种形式的官僚制度。事实上也是因为韦伯展开了对于官僚制度的研究,使得官僚(Bureaucracy)这一词成为常用的社会科学术语[54]。许多现代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都可以追溯至韦伯。当社会学研究述及一个传统的、有著阶级架构的大陆型文官体制时,也经常将之称为“韦伯文官体制”。不过这只是韦伯在他的《经济和社会》(1922)里所提及的其中一种公共行政和政府统治形式,而且韦伯个人并不欣赏这种制度—他只是认为那特别成功和有效罢了。在这本书里,韦伯勾画出了社会学知名的“理性化”概念,亦即从一个价值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转变为一个以目的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法律型权威)。而依据韦伯的说法,不断理性化的结果将会是一个“冰冷的北极夜晚”—人类生活的理性化造成个人陷入了一个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铁的牢笼”(the iron cage)里[55]。韦伯的官僚研究也使他正确预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局,由于自由市场和其机制遭到废止,国家不但没有消失(卡尔·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社会将会达成这个目标)、反而开始了规模惊人的过度官僚化(举例而言,经济短缺的爆发便是证据之一)[56]。
经济史学与社会分层
[编辑]虽然马克斯·韦伯在今天最为人所知的是他身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奠基学者之一,但他也在其他许多领域有不少成就,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韦伯在世时这样精确的学科分类相当少见,而韦伯也自视为主要是一个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仅是第二领域罢了[26][27]。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的是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57]。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韦伯的研究领域也与他的同僚维尔纳·宋巴特相同,宋巴特则将资本主义的崛起归功于犹太教的影响。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他主要贡献(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亦作“暸悟”)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57]。
解释社会学的原则是社会学主要的研究范例之一,支持者和批评者都相当多。这种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不能彻底的归纳和记载,因为研究者必须一直有著概念上的认知才能加以探索之,韦伯将这种条件称为“理想型”(Ideal Type)[57]。这种理想可以这样子归纳:一个理想型 是由许多现象提供的某些特征和成分所组成,但它却不会与任何特定的现象有著完全一样的特征。韦伯的理想型成为他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韦伯承认这种“理想型”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他主张任何想要了解特定社会现象的人都必须有这种理想型,因为与机械物理的现象不同的是,社会科学还牵涉到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而这只有可能以理想型的方法来加以解释。理想型的概念,加上他的反实证主义的立论,可以被视为是他对“理性的经济人”的方法论假设的辩护[57]。
韦伯并且公式化了社会阶层的三大要件理论,主张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和团体(或党派)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要件[58]。
而这三种要件都会影响到韦伯称为“生涯机会”的结果[58]。
韦伯对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贡献:包括了经过认真研究的罗马农业历史,和他在《经济和社会》一书里述及的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韦伯也在书中呈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评。这些方法之后都间接影响了日本学者如大冢久雄与丸山真男的研究路线。最后,他在《经济与历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仔细研究则可以被视为是经济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57]。
社会经济组织与理论
[编辑]在这本著作中使用科层体制或官僚体制来说明一个一种理想的组织型态。韦伯认为在科层体制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依据机械性规则而在一理性系统中所运作的,所谓的系统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因此在这种科层制度下的员工都是经由正式公平的遴选,在组织中亦有严格的分工、明确的职权阶层以及正式的法规与规范,同时具有不徇私的非人情化管理方式[59]。
参考文献
[编辑]- ^ Weber, Max. Roth, Guenther , 编. Economy and Society: Two Volume Set, with a New Foreword by Guenther Roth. 2013-10 [2022-03-14]. ISBN 978-0-520-280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12) (英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Content Pages of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Social Science. hirr.hartsem.edu. [2021-12-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Wolff, Jonathan; Leopold, David. Karl Marx. Zalta, Edward N. (编).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1.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21 [2021-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2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Positivism. obo. [2022-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0) (英语).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5.0 5.1 5.2 5.3 5.4 Kim, Sung Ho. Max Weber. Zalta, Edward N. (编).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1.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21 [2021-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0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经济参考报. jjckb.xinhuanet.com. [2022-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唐爱军.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政治的两种进路. 《学习与探索》. 2014, (4): 23-26 [2021-07-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3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8.0 8.1 8.2 Käsler, Dirk.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 [2022-01-30]. ISBN 978-0-226-4256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01) (英语).
- ^ 9.0 9.1 9.2 9.3 9.4 Max Weber. www.uvm.edu. [2022-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6-0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Cotesta, Vittorio. Max Weber on China: Modernity and Capitalis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8-11-23: 20 [2022-01-30]. ISBN 978-1-5275-222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05) (英语).
- ^ Sica, Alan (2004). Max Weber and the New Century.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 24. ISBN 0765801906.
- ^ 12.0 12.1 12.2 Bendix, Reinhard.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uly 1, 1977: 1 [2006-10-29]. ISBN 978-0-520-03194-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9-29).
- ^ 13.0 13.1 13.2 13.3 13.4 Bendix. Max Weber. : 2.
- ^ 14.0 14.1 Gianfranco Poggi, Weber: A Short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Google Print, p.5[失效链接]
- ^ Marianne Web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2-06-20.. Last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06. Based on Lengermann, P., & Niebrugge-Brantley, J.(1998). The Women Founder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1830-1930. New York: McGraw-Hill.
- ^ Essays in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0-691-00906-3, Google Print, p.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The Early Academic Care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6-10-17.. Last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06. Based on Coser, 1977:237-239.
- ^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Bendix. Max Weber. : 3.
- ^ Ringer, Fritz. 《韋伯學思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新北: 群学. 2013年5月: 2. ISBN 9789866525681 (中文(台湾)).
- ^ 20.0 20.1 Essays in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0-691-00906-3, Google Print, p.22
- ^ Iannaccone, Laurence (1998).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465–1496.
- ^ 22.0 22.1 22.2 Wolfgang J.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ISBN 978-0-226-53400-8, Google Print, p.8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 6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 327.]
- ^ 23.0 23.1 Kaesler, Dirk (1989).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SBN 978-0-226-42560-3
- ^ Gerth, H.H. and C. Wright Mills (194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UK), [2] ISBN 978-0-415-17503-6
- ^ Turner, Stephen (ed) (200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4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26.0 26.1 26.2 William Petersen, Against the Strea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ISBN 978-0-7658-0222-4, 2004, Google Print, p.2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27.0 27.1 Peter R. Baehr, Founders Classics Canon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ISBN 978-0-7658-0129-6, Google Print, p.2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28.0 28.1 John K. Rhoads, Critical Issues in Social Theory, Penn State Press, 1991, ISBN 978-0-271-00753-3, Google Print, p.4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Joan Ferrante, Soci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Thomson Wadsworth, 2005, ISBN 978-0-495-00561-2, Google Print, p.2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30.0 30.1 30.2 Bendix. Max Weber. : 60–61.
- ^ Andrew J. Weigert, Mixed Emotions: Certain Steps Toward Understanding Ambivalence, SUNY Press, 1991, ISBN 978-0-7914-0600-7, Google Print, p.110
- ^ Bendix. Max Weber. : 285.
- ^ 33.0 33.1 33.2 Bendix. Chapter IX: Basic Concepts of Political Sociology. Max Weber.
- ^ Bendix. Max Weber. : 57.
- ^ 35.0 35.1 Bendix. Max Weber. : 54–55.
- ^ Bendix. Max Weber. : 49 [2006-10-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7).
- ^ 37.0 37.1 37.2 Bendix. Max Weber. : 98–99.
- ^ 38.0 38.1 Bendix. Max Weber. : 99–100 [2006-10-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5).
- ^ Bendix. Max Weber. : 124.
- ^ Bendix. Max Weber. : 126–127.
- ^ Bendix. Max Weber. : 135–141.
- ^ 42.0 42.1 Bendix. Max Weber. : 142–158.
- ^ 43.0 43.1 Bendix. Max Weber. : 181.
- ^ Bendix. Max Weber. : 199.
- ^ 45.0 45.1 45.2 45.3 Bendix. Max Weber. : 200–201.
- ^ 46.0 46.1 Bendix. Max Weber. : 204–205.
- ^ Bendix. Max Weber. : 213.
- ^ Bendix. Max Weber. : 256.
- ^ Daniel Warner, 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ISBN 978-1-55587-266-3, Google Print, p.9
- ^ Randal Marlin, Propaganda and the Ethics of Persuasion, Broadview Press, 2002, ISBN 978-1-55111-376-0, Google Print.p15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Wolfgang J. Momms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of Max Weber: Collected Essay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ISBN 978-0-226-53400-8, Google Print, p.46
- ^ Bendix. Max Weber. : 296.
- ^ Bendix. Max Weber. : 303–305.
- ^ Marshall Sashkin, Leadership That Matter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2, ISBN 978-1-57675-193-0, Google Print, p.52[失效链接]
- ^ George Ritzer, 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 Revolutionizing the Means of Consumption, Pine Forge Press, 2004, ISBN 978-0-7619-8819-9, Google Print, p.5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Erik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W. W. Norton & Company, 1963, ISBN 978-0-393-31068-9, Google Print, p.401
- ^ 57.0 57.1 57.2 57.3 57.4 Max Weber, 1864-192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6-12-06. at the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 58.0 58.1 Bendix. Max Weber. : 85–87.
- ^ 郭, 贞. 傳播理論. 新北市: 新闻传播丛书. 2016: 541.
深入阅读
[编辑]-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高承恕:《理性化与资本主义——韦伯与韦伯以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 陈晓林:《学术巨人与理性困境——韦伯、巴柏、哈伯玛斯》(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7)。
- Korotayev A. (安德烈·科罗塔耶夫), Malkov A., Khaltourina D.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acrodynamics. Moscow: URSS, 2006. ISBN 978-5-484-00414-0 [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hapter 6: Reconsidering Weber: Literacy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Guenther Roth|Roth, Guenther (2001). Max Webers deutsch-englische Familiengeschichte. J.C.B. Mohr (Paul Siebeck). ISBN 978-3-16-147557-3
- Marianne Weber|Weber, Marianne (1926/1988). Max Weber: A Biograph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ISBN 978-0-471-92333-6
- Richard Swedberg "Max Weber as an Economist and as a Sociologis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 Richard Swedberg, Max Weber and the Idea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91-07013-1
- Radkau, Joachim (2005). Max Weber The most important Weber-biography on Max Weber's life and torments since Marianne Weber.
- Talcott Parsons, Review of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by Reinhard Bendix,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5, No. 5 (Oct., 1960), pp. 750-752
- T. H. Marshall, Review of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by Reinhard Bendix,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 No. 2 (Jun., 1961), pp. 184-188
外部链接
[编辑]- 韦伯的著作:
- Max Weber-Gesamtausgabe: collected works, in German; homepa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互联网档案馆中马克斯·韦伯的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作品
 来自马克斯·韦伯的LibriVox公共领域有声读物
来自马克斯·韦伯的LibriVox公共领域有声读物- Large collection of the German original tex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A collec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 Max Weber Reference Arch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Max Weber, On Politic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19)
- Large collection of the German original texts
-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secondary literature
- Notes on several of Weber's works, merged into one text file
- Max weber aphorism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有关韦伯的传记:
- 有关韦伯的学说:
- 石元康:〈韦伯的比较宗教学:新教、儒教与资本主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高承恕:〈从对马斯.韦伯(MAX WEBER)的再诠释谈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学的关联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李钧鹏:〈马克斯·韦伯与行动理论:对新教伦理命题的考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张旭东:〈韦伯的立场:市民阶级价值主体的内在矛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5)
- 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9)
- 田辰山:〈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富永健一:〈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