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
| 德意志国防军 Wehrmacht | |
|---|---|
 德国国防军军旗 | |
| 存在时期 | 1935年3月16日-1945年9月20日[a] |
| 国家或地区 | |
| 效忠于 | |
| 部门 | |
| 种类 | |
| 规模 | 1,820万人(总计人数)[3] 723.4万人(1941年)[4] 948万人(1943年)[4] |
| 直属 | |
| 驻军/总部 | |
| 格言 | “主与我们同在” "Gott mit uns"[5] |
| 参与战役 | 西班牙内战 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 |
| 指挥官 | |
| 最高统帅 (1935-1945) | 卡尔·邓尼茨(末任) |
| 国防军总司令 (1935-1938) | |
| 国防部长 (1935-1938) | |
| 最高统帅部总司令 (1935-1945) | |
| 著名指挥官 | 赫尔曼·戈林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威廉·凯特尔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埃里希·雷德尔 卡尔·邓尼茨 埃尔温·隆美尔 |
| 标识 | |
| 铁十字标志变体 |  |
| 德国国防军军徽 | |
| 系列条目 |
| 德国军事历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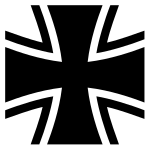 |
| 德国军事主题 |
德国国防军(德语:Wehrmacht,发音:[ˈveːɐ̯maxt] (ⓘ);直译:防御部队[b]),通称国防军,为德意志国1935年至1945年期间的正规武装部队[6],由帝国元首希特勒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直接统领,军种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实际上隶属国防军指挥的纳粹党党卫军,前三者分别受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及空军总司令部指挥。
国防军在二战初期以“闪电战”战术横扫欧洲。通过坦克、步兵和空军的协同作战,德军于欧洲战场上取得了多次胜利。[7]然而因德国领土扩张速度过快,后勤补给线过长,无法及时对前线部队进行补给,导致最终在莫斯科战役中惨败。1942年德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逐渐丧失战略主动权,暴露其在战略、战术和后勤方面,相对于盟军的诸多缺陷。[8]
国防军作为德意志国主要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1800万名士兵服役。[3][9][10]1945年5月,二战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时,国防军军力损失约1130万人[c],其中估计有531.8万人失踪、被杀或在俘虏期间死亡。[11]尽管证据显示不只被审判的人涉嫌违反战争法,但仅有部分国防军高层被追究战争相关的法律责任。[12][13]
背景
[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
[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迫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原德国陆军更名为“和平军”(Friedensheer)[14] 。1919年,德国上议院决议组建规模42万人的“临时国防军”。随后,德国被迫接受了限制严苛的《凡尔赛条约》,条约内规定,德国陆军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海军则为1.5万人,舰队最多拥有6艘战舰、6艘巡洋舰及12艘驱逐舰,且不可成立空军,坦克、重炮及潜艇等皆被禁止使用及制造。1921年3月23日,威玛国防军正式成立。[15]
因条约限制,国防军的兵力被限制在11.5万人。汉斯·冯·塞克特采取了精兵政策,仅保留最优秀的军官。美国历史学家艾伦·米勒和威廉森·莫瑞指出,塞克特在缩编军队的过程中,刻意从总参谋部提拔了一批菁英,而非战争英雄或贵族。塞克特认为,这支精锐部队将是未来扩军的骨干,一旦条约的征兵限制解除,就能迅速扩编。该理念在实质上打造了一支与传统德军不同的新型军队。[16]塞克特于1926年卸任,直至二战爆发前,对国防军的仍有重大的影响。[17]
重建空军军官团
[编辑]《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虽受到条约的限制,但时任国防军总司令的汉斯·冯·塞克特在1920年代初,开始秘密重建空军军官团。军官团认为,空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应扮演多重关键角色,包含夺取制空权、执行战略轰炸,以及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德国空军在1930年代未积极发展战略轰炸能力,非缺乏意愿,而是受到当时经济条件所限。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经济状况受限,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扩张,如需投入大量资源的战略轰炸机。[18]当时德国军方内部存在着资源分配的竞争。由阿尔弗雷德·冯·铁必制海军上将的亲信与门徒、埃里希·雷德尔为代表的领导层,将重心放于重建以往帝国海军的公海舰队,此举压迫部分空军发展的所需资源。1939年前,海军以卡尔·邓尼茨上校为首的“潜艇战”军官在海军内部仍为少数。[19]
规避凡尔赛条约
[编辑]早在1922年,德国便开始暗中规避《凡尔赛条约》中对军事发展的限制。随着《拉帕洛条约》的签订,德国与苏联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合作。[20]1923年,奥托·哈塞少将奉命前往莫斯科,就双方合作的细节进行更深入的磋商。该合作计划涵盖多个层面,德国将协助苏联进行工业现代化,作为回报,苏联则允许德国军官在其境内接受训练。德国的坦克和空军专家得以在苏联境内进行演习,甚至包括在德国本土禁止的研究和生产项目,如化学武器的研发与制造[21],也转移至苏联境内进行。1924年在利佩茨克设立的空军学校,在十年内有逾百名的德国空军人员在此接受了操作维护、导航以及空战等方面的专业训练,成为了德国空军在条约限制下进行秘密发展的基地。1933年9月,随着纳粹党在德国掌权,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德国人才撤离利佩茨克。[22][23]
纳粹执政
[编辑]军队象征纳粹化
[编辑]
1934年8月2日,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去世,阿道夫·希特勒借此机会将总统与总理职位合并,正式成为德国元首,同时掌握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权。早在2月,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便主动下令开除所有在国防军中服役的犹太人[24],展现其对纳粹政权的效忠。同年5月,勃洛姆堡再次主动提议军队制服应采用纳粹标志。[25]
在瓦尔特·冯·赖歇瑙将军的倡议下,国防军开始进行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为军方主动提出。[26]此提议使希特勒感到讶异。誓词的内容如下:“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士兵,我将随时准备为此誓言牺牲我的生命。”[27]
撕毁凡尔赛条约
[编辑]1935年,德国公然无视《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开始大规模的重新武装。3月16日,德国颁布“国防军建设法令”(Gesetz für den Aufbau der Wehrmacht)[28] ,正式宣布重新实行征兵制[29] ,打破了条约对德国军队人数的限制。虽然表面上常备军的规模仍维持在条约规定的约10万人左右,但实际上,每年都会有相当于此规模的新兵接受训练,为未来的扩军做准备。该法令也正式确立了“国防军”(Wehrmacht)的名称,并于1935年5月21日正式将原有的威玛国防军更名为德国国防军。[30]
同年12月,在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推动下,重整军备的计划中增加了48个坦克营[31],德国不断扩充兵员,且积极发展装甲部队等现代化军备。希特勒设定重新军事化的期限为10年,但因其权力的巩固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将期限缩为四年[32],加速了扩军的计划。随着1936年莱茵兰再军事化和1938年的德奥合并,德国的领土大幅扩张,为征兵提供了更大的人力资源。[33]
军种
[编辑]陆军
[编辑]
德国陆军在二战时期进一步改善了陆战的相关战术,将陆军和空军结合为联合兵种。[34]综合“包围战”和“歼灭战”等传统战术。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年内,就取得了许多关键的胜利,使外国记者为该战术创造了一个军事用语“闪电战”(又称闪击战)。[35] 德国于二战开始时,在战场上迅速取得的战果与他们在一战期间取得的优势相吻合,部分人士归功于德军的将领们。[36]
装甲师作为陆军主力部队,对于德军早期的胜利至关重要,陆军早期使用的坦克为一号坦克、二号坦克、LT-35战车及LT-38战车等轻型坦克。后期东线及非洲战场多采用三号坦克及四号坦克。 [37]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仅有少部分部队实现机动化,步兵约九成仍以步行为主,火炮则主要依靠马匹牵引。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依靠着机动化部队,连续赢得波兰战役、威瑟堡行动、比利时战役、法国战役、荷兰战役、南斯拉夫战役和希腊战役,另外掌控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主导权。[38]
1941年12月,希特勒对美国宣战后,轴心国陷入与多个工业强国对抗的局面,而德国的战时经济转型尚未完成。面对敌人的攻势,德军因兵力过度分散、补给线拉长、机动性受限、兵力不足等问题,在1941年至1943年间的一系列关键战役中,如莫斯科战役、列宁格勒围城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突尼斯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接连遭受重大挫败。[39][40]
德国陆军采用任务型战术(Auftragstaktik),强调由上级下达任务目标,而非详细的命令,让前线指挥官在达成目标的前提下,能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势,独立判断并采取最合适的行动,充分发挥其临场反应的能力。尽管在宣传上,德国陆军常被塑造成一支高度现代化的部队,拥有许多先进的科技装备。[41]但实际上德军的新式装备的数量相对有限,并未全面普及到所有部队。尤其东线战场更为明显。由于苏联境内道路及天候影响,德军后勤补给线经常面临问题。四至六成的部队实现了机动化,但大量物资仍需马匹运送。士兵以步行行军,或骑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影响了部队行军速度和作战效率。自1943年起,随着战局对德国不利,德军在东线战场开始转为撤退。[42][43][44]
装甲师作为闪电战成功的关键,国防军将轻型坦克具有的高机动性与空降突击战术相结合,借此快速突破敌军相对薄弱的防线[45],因此装甲师突破敌军防线,将敌军的团级编制与主力分离,使得坦克后的步兵能够迅速歼灭或俘获敌军。[46]
空军
[编辑]
德国空军最初被凡尔赛条约所限制,自希特勒撕毁该条约并大规模扩军后,空军才在赫尔曼·戈林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于1935年。[29]
空军最先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实战经验,为早期闪电战的关键空中力量[d]。德国空军主要集中生产战斗机和小型战术轰炸机,如梅塞施密特的Bf109战斗机及容克斯的Ju 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用来与陆军协同作战。[47]
空军以压倒性数量夺取制空权,轰炸机将攻击前线的指挥所、补给线、仓库和其他支援单位。德国空军也用于投放伞兵部队,如威瑟堡行动。[48][49]由于陆军对希特勒的影响力较大,空军时常受制于陆军,被迫扮演战术支援的角色,失去了发挥战略作用的机会。[50]
二战后期,西方盟军针对德国工业目标,进行全天候的战略轰炸行动,与德国空军进行消耗战[51],德方称其为“帝国保卫战”(Reichsverteidigung)。随着德国战机覆灭,盟军取得制空权,德国陆军失去空中支援,盟军使用战斗机和轰炸机进行攻击和干扰。德国空军在1945年的“底板行动”中蒙受重大损失后,已无能力再发起有效攻击。[52]
海军
[编辑]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禁止使用及建造潜舰,同时限制国家海军的规模只允许拥有六艘战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15]国防军正式成立后,国家海军正式更名为“战争海军”。[53]
随着英德海军协定的签署,德国才被允许扩增海军规模至英国皇家海军吨位的35%,并允许建造一战使用过的U型潜艇[54]。英国签署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安抚德国,而且认为德国海军要到1942年才有可能达到协定内35%的限制。[55][56]
德国海军在二战期间最重要的影响,在大西洋战役中部署了近一千艘潜艇,对盟军的护航船队发动攻击。[57]德国海军的战略目标是透过攻击盟军的运输船队,切断英国的补给线,阻止美国的干涉,借此削弱盟军。[58]在卡尔·邓尼茨的领导下,德国实施了无限制潜艇战,更推动了狼群战术,使多艘潜艇能够协同作战,对盟军的护航船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该潜艇战对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估造成2.3万名人员丧生,以及1300艘船只沉没。[59]1943年初,盟军逐渐发展出反制措施,包括改进护航制度、破解恩尼格玛密码机、改良声纳技术、部署长程轰炸机,以及使用水雷。[60]这些反制措施逐渐扭转了战局,使德国潜艇遭受重大损失,共有757艘潜艇被击沉,超过3万名潜艇艇员丧生。德国潜艇部队最终未能赢得大西洋战役,但其造成的损失仍为重大,迫使盟军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反潜作战,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61]
共存的武装党卫队
[编辑]
起初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存在冲突。国防军担忧党卫军会成为德意志国武装部队的一部分,而导致两团体在如何分配有限的军备供应方面产生分歧。[62] 1938年8月17日,希特勒将党卫军和国防军正式编入法典,以结束两者间的冲突。党卫军的军武大多是“从国防军购买来的”,但于二战前,党卫军与国防军几乎没有任何交流。[63]
国防军被允许检查党卫军的预算与战备状况。在战争动员的情况下,武装党卫军部队属于最高统帅部控制。所有与此相关的决议或行动,皆由希特勒个人自行决定。[64]
虽然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存在冲突,尽管两者隶属于不同的组织,但党卫军中许多高阶军官多自国防军,这使得双方在理念、战术上能迅速达成共识。战争期间,国防军与党卫军士兵在战场上密切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古德里安指出,战争每一天都在继续,陆军和党卫军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意大利和荷兰的军队甚至被指派于党卫军指挥之下。国防军与党卫军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大的改善;但党卫军从未被国防军视为“第四个军种”。[65][66]
兵员募征
[编辑]
国防军的兵力来源采“募征并行”制,1935年至1939年间,共有130万人被征召,240万人自愿参军。[67][68]1935至1945年,国防军服役总人数达1820万人。[3][9][10]德国军事领导层最初目标是建立具有传统普鲁士军事价值观的军队。但由于希特勒不断希望扩大国防军规模,军队不得不接纳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国民,导致内部凝聚力下降,并任命了一些缺乏实战经验的军官。[e][69]
国防军的军官培训和募征成效显著,被视为早期取得胜利,以及在战局对德国不利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战争的重要因素。[70][71]
权力结构
[编辑]1935年至1938年
[编辑]

以法律而言,国防军的最高统帅为阿道夫·希特勒,该职位自1934年8月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后继承至希特勒[72][73],并且以帝国元首的身份担任统帅一职。随着国防军于1935年成立,希特勒将自己封为国防军最高统帅,并持续此职务直至1945年4月30日自杀。后来希特勒任命维尔纳·冯·勃洛姆堡,为德意志国国防部长。[72]自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后,勃洛姆堡辞职国防部长,希特勒因此废除了国防部的指挥权。[74]随后,希特勒成立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OKW),在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领导下,正式取代了国防部。[75]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辖的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分别为陆军总司令部(OKH)、海军总司令部(OKM)和空军总司令部(OKL)。最高统帅部成立之目,为充当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并指挥所有的军事行动,由希特勒担任最高统帅。[76]
曼施坦因等多个高阶军官,主张建立实质意义上三军联合司令部,或任命一位总参谋长,但提议被希特勒拒绝了。即使国防军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希特勒仍拒绝该议案,并表示帝国元帅戈林及希特勒的副官,也不会接受此提议,更不认为自己与其他指挥官为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希特勒拒绝提案的原因,可能为担心此举将会打破他在战略层面上“点石成金”的形象。[77]
1939年至1945年
[编辑]

随着最高统帅部的成立,希特勒巩固了对国防军的控制。虽然于战争初期没有进行太多干预,但希特勒也逐渐参与并干涉到国防军的各种军事行动。[78]
三军总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之间缺乏协调性,各部门的高级将领对其他军种的需求、能力和局限性一无所知。当希特勒为最高统帅时,各指挥部门常被迫互相竞争影响希特勒的战略布局。但影响希特勒的战略布局不仅限于官阶和功绩,也包含希特勒信任的人,反而造成各军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增进国防军的各指挥部门的凝聚力。[50][79]
第二次世界大战
[编辑]二战时期指挥机构
[编辑]二次大战期间,国防军为德意志国的正规武装部队,策划了多项军事行动。1941年以后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KH)成为了国防军东线战场的最高指挥机构,指挥除武装亲卫队外的所有部队的军事行动。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则负责指挥西线相关的军事行动。[80]
北非战场
[编辑]
1940年6月10日,德意两国结盟向英法两国宣战,9月9日,意大利发起埃及战役,企图夺取苏伊士运河,英国随后发起罗盘行动反击。[81][82][83]意大利因在贝达福姆战役中损失惨重,向德国请求援助,德国派遣隆美尔指挥的装甲师协防,随后又增派约2支装甲师及1支摩托化师,希特勒称其为“非洲军团”,北非战役正式转为德意联军对抗英美联军的局面。[84][85][86][87]
起初德意联军从劣势转为优势,连续击破英军守势,但最终仍败于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和突尼斯战役。北非战役宣告结束,奠定了盟军登陆西西里岛,瓦解法西斯意大利政权的基础。[88][89][90]
东线战场
[编辑]
东线国防军的主要战役包括:
- 入侵捷克
- 波兰战役(白色方案):为纳粹德国、苏联及斯洛伐克联合的军事行动。
- 入侵南斯拉夫及希腊战役(玛莉塔作战)
- 巴巴罗萨行动(苏德战争):为国防军陆军在二战期间最大及阵亡人数最多的战役。这场与苏联红军的战事对欧洲轴心国于二战的战略造成重大的影响,因苏联及西线英美联军随后皆开始展开反攻,而苏联的东线战场对物资的需求在二战中比其他战场都高。同时东线战场面积之大亦令纳粹德国须将战区分由“北方集团军”、“中央集团军”、“南方集团军”及“挪威军团”四大部队分摊战略策划的工作。
- 高加索战役
- 库尔斯克会战
- 基辅会战
- 巴格拉基昂行动
- 部分在东线的反苏联游击队行动及大规模镇压占领区后反抗部队的相关行动,由武装亲卫队负责清算。
希特勒要求国防军要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甚至有时需同时指挥3个战区作战,造成资源分摊不均且不足,1944年起德国于巴巴罗萨行动中逐渐处于劣势,使进行本土防御变为不可能。[91]
西线战场
[编辑]
西线国防军主要战役包括:
战争以陆战为主的,结束后就演变成了两方面的进攻,一是由德国空军发动不列颠战役攻击英国,另一是由德国海军针对对英国的物资输送航线进行战略打击。
- 诺曼底登陆战:1944年盟军成功登陆欧洲大陆,从西线开辟第二战场。
- 德国空军分别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及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取得胜利,但随后战败于不列颠空战中。自1941年起至1943年末,德国空军在对抗苏联空军的长时间空战中,影响了对抗英国皇家空军的行动。而自1944年夏季起,盟军的空军部队在3个欧洲战场皆取得了主动权。在不列颠战役中,德国空军起初企划炸毁英军机场及与英军打消耗战为早期的军事目标,但在战役之中陷入自身损失比皇家空军还快的困境中。虽然战争期初德军站处优势,但德国空军不像英国空军恢复速度极快,甚至可以抵消损失率。自英军空袭柏林后,希特勒命令轰炸英国城市作为报复,反而令德国空军的目标由英国皇家空军转为英国平民,使皇家空军得以获得喘息之机重建空中力量,以抗衡德军对英国领空的威胁。
- 大西洋战役中德国海军于前期取得胜利,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表示,在整个二战期间唯一能让他感到英国生存受到真正威胁的,就是德国海军U艇的袭击。
国防军伤亡统计
[编辑]
1935年至1945年间,史学家吕迪格·奥弗曼斯曾提出,德意志国防军约有1820万人,反映了该期间服役于德意志国防军的总人数。[9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防军共有超过600万名士兵战伤,约1100万人成为战俘。其中以德军身份作战的德国人及他国志愿军中,约有553.3万人阵亡、因伤去世、受俘期间去世或失踪。其中也包括了21.5万名在德占期间被征召的苏联平民[93]。
自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德军伤亡急剧攀升。短短一个月内,约18万德军战死。最终统计,德军共损失530万兵力,其中逾八成损失于战争末期,七成五的士兵死于苏德战场。1945年1月至2月,盟军逐渐推进至柏林,德军更损失了约120万人。[94]
1941年至1943年间,德军在西线战场的阵亡人数占总阵亡人数的3%以下,自1944年上升至14%。即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在东线战场仍约损失68.5%的兵力。苏联红军的快速反攻对持续撤退的德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95]
战后除天灾和战争而造成的伤亡外,有约2万名国防军士兵被军事法庭处死。另外苏联自行处决13.5万人[f]、法国处决102人、美国处决146人,英国则处决40人。[96][97][98]
战后发展
[编辑]国防军的瓦解
[编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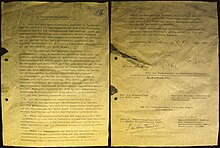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德军于1945年5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仍有一些部队继续活动(如在挪威的国防军),有些则在盟军指挥下担任警务工作。[99]最后一个向盟军投降的德军部队,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一个孤立气象站,于9月4日向挪威救援船队正式投降。[100]
1945年9月20日,盟国管制理事会(ACC)第2号公告宣布:“所有德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党卫队、冲锋队、安全局和盖世太保等所有组织、人员和机构,包括总参谋部、军官团、预备役军团、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组织以及所有其他军事和准军事组织,以及所有用于在德国保持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应根据盟军代表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彻底和废除。”[101]1946年8月20日,ACC第34号法令正式解散国防军[102],该法令宣布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陆军总司令部、航空部和海军总司令部被“解散、彻底清算并且宣布为非法组织”。[103]
国防军战斗力的评价
[编辑]二战结束初期,由于德国战败,许多人倾向于贬低德军的战斗力,强调盟军优秀的战斗力。[10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了德军在战争中的表现,对其战斗力和战术层面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甚至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7],原因为他们经常能在兵力、火力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对敌军造成更大的打击。[105][106]
以色列军事史学家马丁·范克勒维尔德,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分析了德军的能力,提出德军是一支出色的战斗组织。在士气、冲劲、部队凝聚力和韧性方面,德军在二十世纪中可能领先世界。[107]德国史学家罗尔夫·迪特尔·穆勒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德军的战斗力远超人们先前的认知。[108]苏联档案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此观点,因为德军的对手远比当时德国军官所认为的强大许多。战略思想家柯林·S·格雷则强调了德军出色的战术和作战能力。因为多次的胜利,德国高层开始变得过于自信,要求德军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且德军对闪电战的过度依赖,让苏联人学会了此战术,反而被用来对付德军。[109]
国防军无罪论
[编辑]二战结束后,部分前国防军军官、退伍军人团体,以及极右翼思想的作家,开始宣扬“国防军无罪论”(Clean Wehrmacht)。称国防军是一个非政治化的正规军事组织,与纳粹政权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毫无关系,或仅有极少数个案。为了从理论中获利,洗脱自身罪责,武装亲卫队的退伍军人也附和此说法,甚至宣称武装亲卫队实际上是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仅“为国作战”。武装亲卫队的退伍军人组织“互助会”(HIAG)也同样推广此论述,企图塑造其成员仅是“尽忠职守”的形象。[110]
政治关系
[编辑]政变
[编辑]
起初,国防军对希特勒的领导几乎没有异议,因为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试图恢复军队的荣誉。[111]然而,随着希特勒的扩张野心日益显露,军内开始出现反对声浪。1938年,奥斯特阴谋便是最早的大规模抵抗行动之一,参与者担心希特勒过早发动战争将使德国走向灭亡。[112]但随德军在二战初期以胜利告捷,希特勒的威信达到巅峰,抵抗声浪一度消失。[113]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德军的劣势逐日增加,希特勒的领导力也受到挑战。[113]抵抗运动再度兴起,并于1944年7月20日达到顶峰。施陶芬贝格等人发起的刺杀行动,虽以失败告终,却展现了德军内部对纳粹政权的强烈不满。这场政变导致数千名国防军将领被处死。[114]标准军礼由纳粹礼正式取代,成为纳粹统治的象征。[115]
人道救援行动
[编辑]
在纳粹政权统治下,并非所有国防军成员都认同种族灭绝的政策。安东·施密德中士利用职务之便,为250多名犹太儿童伪造证件,协助他们从维尔纽斯隔都逃脱。阿尔伯特·巴特尔则在普热梅希尔集中营,阻止党卫军进入,避免了屠杀的悲剧,并将超过百名犹太人安置在自己的军事基地。威尔姆·欧森菲德上尉则将犹太裔作曲家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藏匿于波兰的城市废墟中,并提供其生活必需品,使其得以幸存。[116]
战争罪行
[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
[编辑]

虽然公认党卫军是践踏人权最为严重的部队,但国防军所犯下的罪行仍不可抹灭。在对苏战争期间,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下令,针对游击队的袭击,德军应采取“武力反击措施”[117],实际意味着对平民的报复,许多村庄因此遭到屠杀。此外,德军在占领区实施的粮食和饲料征收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造成数十万至数百万苏联平民饿死。[118]历史学家托马斯·库纳估计,德军在苏联境内发起的“反游击战”,导致约30万至50万名平民丧生。[119]英国情报部门通过截获德军的无线电通讯,证实德军参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等违反国际法的暴行。[120][121]
国防军的战俘营总体上满足了《日内瓦公约》内规定的人道主义[122];但波兰和苏联战俘的关押环境,相对于西方战俘恶劣许多。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数个月内,德军俘虏了约320万名苏联战俘,其中超过八成(约280万人)死于德国的战俘营中。[123]
克里特岛战役结束后,隶属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部队,于1941年6月2日在克里特岛的孔多马里村进行屠杀,至少有23名村民遇害,史称“孔多马里村屠杀”。隔日,该部队在指挥官司徒登(Kurt Student)的命令下,对坎达诺斯村进行报复性摧毁,估计约有180名平民丧生,包含妇女和儿童。此外,在1943年至1945年间,德国第1空降猎兵师的成员在意大利也犯下多起战争罪行,其中包含皮耶特兰谢里村屠杀事件[124][125]。
战后审判
[编辑]
纽伦堡审判明确指出,虽然国防军最初并非犯罪组织,但在二战期间,德军却参与了多起战争罪行,成为纳粹屠杀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德军高层将领,如威廉·凯特尔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因战争罪行被处决。[126]
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界逐渐形成共识,认为在纳粹“生存空间”理论的驱使下,东线德军犯下了远超西线的战争罪行,包括对平民的屠杀、虐待苏联战俘等行为。[127]90年代,以魏玛展览(Wehrmachtsausstellung)为代表,关于德军战争罪行的展览在德国社会引发了争议,争论如何看待德军在二战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面对历史。[128]
近年来,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质疑再起,以色列历史学家奥马尔·巴托夫曾提出观点[129],主张德军并非有预谋的进行种族灭绝,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有被夸大之疑。德军为正规武装部队,其成员多半遵循军事命令,仅有少数人士违反国际法,不应以此概括全体德军,该说法为错误的。[130]反而认为国防军是一个犯罪组织[131],英国历史学家理察·埃文斯和伊恩·克肖等人,透过大量的历史证据认同巴托夫的说法,强调德军是纳粹屠杀计划的执行者。埃文斯和克肖指出,德军的任务不仅是为国作战,更是为所谓的“雅利安人”拓展“生存空间”。据德军的信件及回忆录,呈现德军对斯拉夫人的种族歧视,并将其视为劣等民族。 [132][133]
德军在占领区建立了大规模的军妓院[134],强征平民百姓充当慰安妇。[135]德国空军也与集中营有着密切的关联,向集中营派遣卫兵,并利用集中营的劳工生产军需物资。[136]
参见
[编辑]注释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1946a年),第81页
- ^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1946b年),第63页
- ^ 3.0 3.1 3.2 Overmans(2004年),第215页
- ^ 4.0 4.1 Müller(2016年),第36页
- ^ Armbrüster(2005年),第64页
- ^ Taylor(1995年),第90–119页
- ^ 7.0 7.1 Van Creveld(1982年),第3页
- ^ Müller(2016年),第58–59页
- ^ 9.0 9.1 Wette(2006年),第77页
- ^ 10.0 10.1 Müller(2016年),第16页
- ^ Fritz & 2011,第470页
- ^ Wette & 2006,第195–250页
- ^ USHMM & n.d.
- ^ Wheeler-Bennett(1967年),第60页
- ^ 15.0 15.1 Craig(1980年),第424–432页
- ^ Murray & Millett(2001年),第22页
- ^ Wheeler-Bennett(1967年),第22页
- ^ Murray & Millett(2001年),第33页
- ^ Murray & Millett(2001年),第37页
- ^ Wheeler-Bennett(1967年),第131页
- ^ Zeidler(2006年),第106–111页
- ^ Müller(2016年),第10页
- ^ Cooper(1981年),第382–383页
- ^ Förster(1998年),第268页
- ^ Wheeler-Bennett(1967年),第312页
- ^ Kershaw(1997年),第525页
- ^ Broszat等(1999年),第18页
- ^ Müller(2016年),第7页
- ^ 29.0 29.1 Fischer(1995年),第408页
- ^ Stone(2006年),第316页
- ^ Tooze(2006年),第208页
- ^ Müller(2016年),第12–13页
- ^ Müller(2016年),第13页
- ^ Palmer(2010年),第96–97页
- ^ Deighton(1996年),第146-147页
- ^ Mosier(2006年),第11–24页
- ^ (英文)Heer - The Army 1935-1945. feldgrau.com. [2012-06-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2-06).
- ^ Frieser(2005年),第4–5页
- ^ Atkinson(2002年),第536页
- ^ Jukes(2002年),第31页
- ^ Zeiler & DuBois(2012年),第171–172页
- ^ Zhukov(1974年),第110–111、142页页
- ^ Corrigan(2011年),第353页
- ^ Bell(2011年),第95, 108页
- ^ Trueman(2015年)
- ^ History.com Editors(2010年)
- ^ Tooze(2006年),第125–130页
- ^ Outze(1962年),第359页
- ^ Merglen(1970年),第26页
- ^ 50.0 50.1 Hayward(1999年),第106页
- ^ Darling(2008年),第181页
- ^ Girbig(1975年),第112页
- ^ documentArchiv.de(2004年),§2
- ^ Maiolo(1998年),第35–36页
- ^ Müller(2016年),第17页
- ^ Maiolo(1998年),第57–60页
- ^ Müller(2016年),第71–72页
- ^ Müller(2016年),第72页
- ^ Hughes & Costello(1977年)
- ^ Hickman(2015年)
- ^ Niestle(2014年),Introduction
- ^ Christensen,Poulsen & Smith(2015年),第433, 438页
- ^ Stein(2002年),第20–21页
- ^ Stein(2002年),第22页
- ^ Christensen,Poulsen & Smith(2015年),第438页
- ^ Christensen,Poulsen & Smith(2015年),第437页
- ^ U.S. War Department(1945年),第I-57页
- ^ Müller(2016年),第12页
- ^ Müller(2016年),第13–14页
- ^ Miller(2013年),第292–293页
- ^ Kjoerstad(2010年),第6页
- ^ 72.0 72.1 documentArchiv.de(2004年),§3
- ^ Broszat(1985年),第295页
- ^ Stein(2002年),第18页
- ^ Megargee(2000年),第41–42页
- ^ Hayward(1999年),第105–106页
- ^ Hayward(1999年),第104–105页
- ^ Müller(2016年),第18–20页
- ^ Hayward(1999年),第105页
- ^ Grier(2007年),第121页
- ^ Playfair等(2004a年),第109、260-261、264页
- ^ Macksey(1971年),第38页
- ^ Wavell 第37628號憲報. 伦敦宪报 (Supplement). 1946年7月25日.
- ^ Playfair(2004a年),第361–362页
- ^ Jentz(1998年),第82页
- ^ Rommel,第109页
- ^ Walker(2003年),第14页
- ^ Playfair等(2004a年),第480页
- ^ Montanari(1993年),第838页
- ^ 白虹, 二战全史. 北非閃击. 新华书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年第一版: 236页. ISBN 978-7-5113-4757-2.
- ^ Fritz(2011年),第366–368页
- ^ Overmans(2004年),第335页
- ^ Rűdiger Overmans.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Wikipedia. 2000: 335 [2013-11-16]. ISBN 3-486-5653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0-19).
- ^ Frank Biess (2006).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9. ISBN 978-0-691-12502-2.
- ^ Jeffrey Herf (2006).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52. ISBN 978-0-674-02175-4
- ^ Krivosheev(2010年),第219页
- ^ Mikhalev(2000年),第23页
- ^ Müller(2016年),第30页
- ^ Fischer(1985年),第322, 324页
- ^ Barr(2009年),第323页
- ^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1946a年)
- ^ Large(1996年),第25页
- ^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1946b年)
- ^ Hastings(1985年)
- ^ O'Donnell(1978年),第61页
- ^ Gray(2007年),第148页
- ^ Van Creveld(1982年),第163页
- ^ Bönisch & Wiegrefe(2008年),第51页
- ^ Gray(2002年),第21–22页
- ^ Wienand(2015年),第39页
- ^ Balfour(2005年),第32页
- ^ Jones(2008年),第73–74页
- ^ 113.0 113.1 Bell(2011年),第104–105、107页
- ^ Kershaw(2001年),第693页
- ^ Allert(2009年),第82页
- ^ Szpilman(2002年),第222页
- ^ Förster(1989年),第501页
- ^ Megargee(2007年),第121页
- ^ Smith(2011年),第542页
- ^ Datner(1964年),第67–74页
- ^ Datner(1964年),第20–35页
- ^ Le Faucheur(2018年)
- ^ Davies(2006年),第271页
- ^ MacDonald, C.A. The lost battle – Crete, 1941. Free Press, 1993, ISBN 0-02-919625-6.
- ^ Kiriakopoulos, G.C. The Nazi Occupation of Crete: 1941–1945,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ISBN 0-275-95277-0.
- ^ Hebert(2010年),第216–219页
- ^ Wildt,Jureit & Otte(2004年),第30页
- ^ Wildt,Jureit & Otte(2004年),第34页
- ^ Bartov(1999年),第131–132页
- ^ Bartov(2003年),第xiii页
- ^ Bartov(1999年),第146页
- ^ Evans(1989年),第58–60页
- ^ Shepherd(2003年),第49–81页
- ^ Joosten(1947年),第456页
- ^ Lenten(2000年),第33–34页
- ^ Gmyz(2007年)
参考书目
[编辑]- Montanari, Mario. El Alamein. Le operazioni in Africa Settentrionale III. Roma: Stato Maggiore dell'esercito, Ufficio Storico. 1993. OCLC 313319483.
- Walker, Ian W. Iron Hulls Iron Hearts. Trowbridge: The Crowood Press. 2003. ISBN 978-1-86126-646-0.
- Jentz, Thomas L. Tank Combat in North Africa: The Opening Rounds, Operations Sonnenblume, Brevity, Skorpion and Battleaxe, February 1941 – June 1941. Schiffer Publishing. 1998. ISBN 978-0-7643-0226-8.
- Playfair, Major-General I. S. O.; et al. Butler, J. R. M. , 编. The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The Early Successes Against Italy (to May 1941).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 I. London: HMSO. 1954. OCLC 888934805.
- Playfair, Major-General I.S.O.; Molony, Brigadier C.J.C.; Flynn, Captain F.C. RN & Gleave, Group Captain T.P. Butler, J.R.M , 编. The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The Early Successes Against Italy (to May 1941).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 I. Naval & Military Press. 2004a [1st. pub. HMSO 1954]. ISBN 978-1-84574-065-8.
- Macksey, Major Kenneth. Beda Fomm: The Classic Victory. Ballantin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olent Century. Ballantine. 1971. OCLC 637460844.
- Grier, Howard D. Hitler, Dönitz, and the Baltic Sea.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ISBN 978-1-59114-345-1.
- Allert, Tilman. The Hitler Salute: On the Meaning of a Gesture. 由Chase, Jefferson翻译. Picador. 2009. ISBN 978-0-312-42830-3.
-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 Enactments and Approved Papers of the Control Council and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DF). Library of Congress. 1946a.
-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 Enactments and Approved Papers of the Control Council and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DF). Library of Congress. 1946b.
- Armbrüster, Thoma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Germany.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ISBN 978-0-7546-3880-3.
- Atkinson, Rick. An Army at Dawn: The War in North Africa, 1942–1943. Abacus. 2002. ISBN 978-0-349-11636-5.
- Balfour, Michael. Withstanding Hitl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ISBN 978-0-415-00617-0.
- Barr, W. Wettertrupp Haudegen: The last German Arctic weather station of World War II: Part 2. Polar Record. 2009, 23 (144): 323–334. doi:10.1017/S0032247400007142.
- Bartov, Omer. The Eastern Front, 1941–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ISBN 978-0-312-22486-8.
- Bartov, Omer.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ISBN 978-0-19-506879-5.
- Bartov, Omer.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Leitz, Christian (编). The Third Reich: The Essential Readings. London: Blackwell. 1999: 129–150. ISBN 978-0-631-20700-9.
- Bartov, Omer. Germany's War and the Holocaust: Disputed Histories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78-0-631-20700-9.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978-0-631-20700-9. - Bartrop, Paul R. Resisting the Holocaust: Upstanders, Partisans, and Survivors. ABC-CLIO. 2016. ISBN 978-1-61069-878-8.
- Bell, P.M.H. Twelve Turning Point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300-18770-0.
- Beyda, Oleg. 'Iron Cross of the Wrangel's Army': Russian Emigrants as Interpreters in the Wehrmacht.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14, 27 (3): 430–448. S2CID 144274571. doi:10.1080/13518046.2014.932630.
- Bickford, Andrew. Fallen Elites: The Military Other in Post–Unification German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8047-7396-6.
- Biess, Frank.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691-12502-2.
- Bidlingmaier, Gerhard. KM Admiral Graf Spee. Warship Profile 4. Windsor, England: Profile Publications. 1971: 73–96. OCLC 20229321.
- Böhler, Jochen. Auftakt zum Vernichtungskrieg. Die Wehrmacht in Polen 1939.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6. ISBN 978-3-596-16307-6 (德语).
- Bönisch, Georg; Wiegrefe, Klaus. Schandfleck der Geschichte. Der Spiegel. 2008, (15): 50–52 [2019-01-15] (德语).
- Bos, Pascale. Feminists Interpreting the Politics of Wartime Rape: Berlin, 1945; Yugoslavia, 1992–1993.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06, 31 (4): 996–1025. S2CID 144605884. doi:10.1086/505230.
- Broszat, Martin. The Hitler State: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Longman. 1985. ISBN 978-0-582-48997-4.
- Broszat, Martin; Buchheim, Hans; Jacobsen, Hans-Adolf; Krausnick, Helmut. Anatomie des SS-Staates Vol.1.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德语).
- Christensen, Claus Bundgård; Poulsen, Niels Bo; Smith, Peter Scharff. Waffen-SS : Europas nazistiske soldater [Waffen-SS: Europe's Nazi soldiers] 1. Lithuania: Gyldendal A/S. 2015. ISBN 978-87-02-09648-4 (丹麦语).
- Cooper, Matthew. The German Air Force, 1933–1945: An Anatomy of Failure. Jane's Publications. 1981. ISBN 978-0-53103-733-1.
- Corrigan, Gordo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 Atlantic. 2011. ISBN 978-0-857-89135-8.
- Craig, Gordon. Germany, 1866–1945
 .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ISBN 978-0-19-502724-2.
.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ISBN 978-0-19-502724-2. - Darling, Kev. Aircraft of the 8th Army Air Force 1942–1945. USAAF Illustrated. Big Bird Aviation. 2008. ISBN 978-0-9559840-0-6.
- Datner, Szymon. Crimes against Prisoners-of-War: Responsibility of the Wehrmacht. Warszawa: Zachodnia Agencja Prasowa. 1964. OCLC 5975828.
- Datner, Szymon. 55 Dni Wehrmachtu w Polsce [55 days of the Wehrmacht in Poland]. Warszawa: Wydawn, Ministerstwa Obrony Narodowej. 1967. OCLC 72344547 (波兰语).
- Davies, Norman. Europe at War 1939–1945: No Simple Victory. London: Pan Books. 2006. ISBN 978-0-330-35212-3.
- Davies, W. German Army Handbook. Shepperton, Surrey: Ian Allan Ltd. 1973. ISBN 978-0-7110-0290-6.
- Duiker, William J. The Crisis Deepens: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Shepperton, Surrey: Cengage Learning. 2015. ISBN 978-1-285-44790-2.
- Evans, Anthony A. World War II: An Illustrated Miscellany. Worth Press. 2005. ISBN 978-1-84567-681-0.
- Evans, Richard J.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1989. ISBN 978-0-394-57686-2.
-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at War
 . New York, NY: Penguin. 2008. ISBN 978-0-14-311671-4.
. New York, NY: Penguin. 2008. ISBN 978-0-14-311671-4. - Fest, Joachim. Plotting Hitler's Death—The 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ISBN 978-0-8050-4213-9.
- Fischer, Alexander. Teheran – Jalta – Potsdam: Die sowjetischen Protokolle von den Kriegskonferenzen derGrossen Drei.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5. ISBN 978-3-8046-8654-0 (德语).
- Fischer, Klaus. Nazi Germany: A New History. New York, NY: Continuum. 1995. ISBN 978-0-82640-797-9 (德语).
- Frieser, Karl-Heinz. Blitzkrieg-legende: der westfeldzug 1940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 由Greenwood, J. T.翻译.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ISBN 978-1-59114-294-2.
- Förster, Jürgen. The Wehrmacht and the War of Extermina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Marrus, Michael (编). The Nazi Holocaust Part 3 The "Final Solu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ss Murder vol.2. Westpoint: Meckler Press. 1989: 494–520. ISBN 978-0-88736-255-2.
- Förster, Jürgen. Complicity or Entanglement? The Wehrmacht, the War and the Holocaust. Berenbaum, Michael; Peck, Abraham (编). The Holocaust and History The Known, the Unknown, the Disputed and the Reexamined
 .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6–283. ISBN 978-0-253-33374-2.
.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6–283. ISBN 978-0-253-33374-2. - Förster, Jürgen. The German Military's Image of Russia. Erickson, Ljubica; Erickson, Mark (编). Russia War, Peace and Diplomac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4: 117–129. ISBN 978-0-297-84913-1.
- Fritz, Stephen.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1. ISBN 978-0-8131-3416-1.
- Garzke, William H.; Dulin, Robert O. Battleships: Axis and Neutral Battleship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ISBN 978-0-87021-101-0.
- Girbig, Werner. Six Months to Oblivion: The Eclipse of the Luftwaffe Fighter Force Over the Western Front, 1944/45.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1975. ISBN 978-0-88740-348-4.
- Goda, Norman. Black Marks: Hitler's Bribery of his Senior Officers During World War II. Kreike, Emmanuel; Jordan, William Chester (编). Corrupt Histories. Toronto: Hushion House. 2005: 413–452. ISBN 978-1-58046-173-3.
- Gray, Colin. Defining and Achieving Decisive Victory (PDF).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2019-01-11]. ISBN 978-1-58487-089-0.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8-01-27).
- Gray, Colin. War, Pea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Routledge. 2007. ISBN 978-0-415-59487-5.
- Greenwald, Maurine Weiner.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1939-1945 by Leila J. Rupp.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1, 55 (1): 124–126. JSTOR 3114466. S2CID 154515739. doi:10.2307/3114466.
- Grossmann, Atina. Jews, Germans, 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1-40083-274-3.
- Harrison, Mark.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19-01-09]. ISBN 978-0-521-78503-7.
- Hartmann, Christian. Operations Barbarossa: Nazi Germany's War in the East, 1941–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ISBN 978-0-19-966078-0.
- Hastings, Max. Their Wehrmacht was better than our Army. The Washington Post. 1985-05-05.
- Hayward, Joel. A case study in early joint warfare: An analysis of the Wehrmacht's Crimean campaign of 1942.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9, 22 (4): 103–130. doi:10.1080/01402399908437771.
- Hayward, Joel. Adolf Hitler and Joint Warfare (Upper Hutt: Military Studies Institute, 2000.
- Hebert, Valerie. Hitler's Generals on Trial: The Last War Crimes Tribunal at Nuremberg.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ISBN 978-0-7006-1698-5.
- Herbermann, Nanda; Baer, Hester; Baer, Elizabeth Roberts. The Blessed Abyss: Inmate #6582 in Ravensbruck Concentration Camp for Women (Google Book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11-01-12]. ISBN 978-0-8143-2920-7.
- Herf, Jeffrey.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674-02175-4.
-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ISBN 978-0-8419-0832-1.
- Hinsley, F. H.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ts influence on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bridged 2nd rev. London: HMSO. 1994 [1993]. ISBN 978-0-11-630961-7.
- Huber, Ernst Rudolf.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2.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51 - 1918. Kohlhammer Verlag. 2000. ASIN B0000BQQHL.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2) (德语).
- Hughes, Terry; Costello, John. Battle of the Atlantic. HarperCollins Distribution Services. 1977. ISBN 978-0-00-216048-3.
- Jones, Nigel. Countdown to Valkyrie: The July Plot to Assassinate Hitler. Philadelphia, PA.: Casemate. 2008. ISBN 978-1-84832-508-1.
- Joosten, Paul A. (编).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PDF) 7. Nuremberg, Germany: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 Nuremberg. 1947. OCLC 300473195.
- Jukes, Geoffrey.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Oxford: Osprey. 2002. ISBN 978-1-84176-391-0.
- Kershaw, Ian.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978-0-521-56521-9.
- Kershaw, Ian.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ISBN 978-0-39332-252-1.
- Kershaw, Ian. Hitler: A 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ISBN 978-0-393-06757-6.
- Killen, John. The Luftwaffe: A History. South Yorkshire: Pen & Sword Military. 2003. ISBN 978-1-78159-110-9.
- Kitchen, Martin. Nazi Germany at War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ISBN 978-0-582-07387-6.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ISBN 978-0-582-07387-6. - Kjoerstad, Ola. German officer education in the interwar years (PhD diss.) (PDF).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10.
- Kompisch, Kathrin. Täterinnen. Frau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öhlau Köln. 2008. ISBN 978-3-412-20188-3 (德语).
- Krivosheev, Grigori F. Russia & USSR at War in the 20th century. Moscow: Veche. 2010. ISBN 978-5-9533-3877-6 (俄语).
- Lampe, John R. Yugoslavia as History: Twice There Was a Country 2n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96]. ISBN 978-0-521-77401-7.
- Large, David Clay. Germans to the Front: West German Rearmament in the Adenauer Er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ISBN 978-0-80784-539-4.
- Leitz, C. M. Arms Exports from the Third Reich, 1933-1939: The Example of Krupp.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Blackwell Publishers). February 1998, 51 (1): 133–154. JSTOR 2599695. doi:10.1111/1468-0289.00086.
- Lenten, Ronit. Israel and the Daughters of the Shoah: Reoccupying the Territories of Silence. Berghahn Books. 2000. ISBN 978-1-57181-775-4.
- Maiolo, Joseph. The Royal Navy and Nazi Germany, 1933–39 A Study in Appeas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ISBN 978-0-312-21456-2.
- Markovich, Slobodan G. Memories of Victimhood in Serbia and Croatia from the 1980s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El-Affendi, Abdelwahab (编). Genocidal Nightmares: Narratives of Insecurity and the Logic of Mass Atrocities. New York City: Bloomsbury. 2014: 117–141. ISBN 978-1-62892-073-4.
- Marston, Daniel; Malkasian, Carter (编). Counterinsurgency in Modern Warfare. Osprey Publishing. 2008. ISBN 978-1-84603-281-3.[永久失效链接]
- Megargee, Geoffrey P. Triumph of the Null: Struc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Command of German Land Forces, 1939-1945. War in History. 1997, 4 (1): 60–80. S2CID 159950260. doi:10.1177/096834459700400104.
- Megargee, Geoffrey P.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as: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7006-1015-0.
- Megargee, Geoffrey P. War of Annihilation: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Rowman & Littelefield. 2007. ISBN 978-0-7425-4482-6.
- Merglen, Albert. Geschichte und Zukunft der Luftlandetruppen. Rombach. 1970. ASIN B0000BSMDD (德语).
- Mikhalev, Sergey Nikolaevich. Liudskie poteri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Statisticheskoe issledovanie [Human Losses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1941–1945 A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Krasnoyarsk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2000. ISBN 978-5-85981-082-6 (俄语).
- Miller, Charles A. Destructivit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ilitary Effectiveness in Conventional Combat. (PhD dis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DF). Duke University. 2013.
- Mosier, John. Cross of Ir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War Machine, 1918–1945.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6. ISBN 978-0-80507-577-9.
- Müller, Klaus-Jürgen.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Studies in the Army's Relation to Naz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ISBN 978-0-7190-1071-2.
- Müller, Rolf-Dieter. The Unknown Eastern Front: The Wehrmacht and Hitler's Foreign Soldiers. New York: I.B.Tauris. 2014. ISBN 978-1-78076-890-8.
- Müller, Rolf-Dieter. Hitler's Wehrmacht, 1935–1945.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ISBN 978-0-81316-738-1.
- Murray, Williamson; Millett, Allan Reed. A War to Be Won: 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 978-0-674-00680-5.
- Neitzel, Sönke; Welzer, Harald. Soldaten: On Fighting, Killing, and Dying – The Secret WWII Transcripts of German POW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ISBN 978-0-30795-812-9.
- Niestle, Axel. German U-Boat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Details of Destruction.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4. ISBN 978-1-84832-210-3.
- O'Donnell, H. K. Smith, Robert W. , 编. A GENIUS FOR WAR: Review. Marine Corps Gazette. June 1978, 62 (6): 60–61. ISSN 0025-3170.
- Outze, Børge. Danmark under anden verdenskrig. Copenhagen: Hasselbalch. 1962. ISBN 978-87-567-1889-9 (丹麦语).
- Overmans, Rüdiger.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Oldenbourg. 2004. ISBN 978-3-486-20028-7 (德语).
- Palmer, Michael A. The German Wars: A Concise History, 1859–1945.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0. ISBN 978-0-76033-780-6.
- Pavlowitch, Stevan K. Hitler's New Disord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 New York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1-85065-895-5.
- Richards, Denis. VI The Struggle at Sea: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Convoy Routes, the Anti-Shipping Offensive and the Escape of the 'Scharnhorst' and 'Gneisenau'. Royal Air Force 1939–1945: The Fight at Odds.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ilitary Series I pbk. London: HMSO. 1974: 94–116 [1953] [2016-10-15]. ISBN 978-0-11-771592-9.
- Schoeps, Karl-Heinz. Holocaust and Resistance in Vilnius: Rescuers in "Wehrmacht" Uniforms. German Studies Review. 2008, 31 (3): 489–512. JSTOR 27668589.
- Schulte, Theo. The German Army and Nazi Policies in Occupied Russia. Oxford: Berg. 1989. ISBN 978-0-85496-160-3.
- Shepherd, Ben H. The Continuum of Brutality: Wehrmacht Security Divisions in Central Russia, 1942. German History. 2003, 21 (1): 49–81. doi:10.1191/0266355403gh274oa.
- Shepherd, Ben H. War in the Wild East: the German Army and Soviet Partis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978-0-674-01296-7.
- Sigmund, Anna-Maria. Les femmes du IIIe Reich. Jean-Claude Lattès. 2004. ISBN 978-2-7096-2541-8 (法语).
- Smelser, Ronald; Davies, Edward. The Myth of the Eastern Front: the Nazi-Soviet War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978-0-521-83365-3.
- Smith, Helmut Wals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19-923739-5.
- Stackelberg, Roderick.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azi German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ISBN 978-0-41530-861-8.
- Stein, George. The Waffen-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1945. Cerberus Publishing. 2002 [1966]. ISBN 978-1-84145-100-8.
- Stone, David J. Fighting for the Fatherland: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Soldier from 1648 to the Present Day
 . Herndon, VA: Potomac Books. 2006. ISBN 978-1-59797-069-3.
. Herndon, VA: Potomac Books. 2006. ISBN 978-1-59797-069-3. - Strohn, Matthias.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ei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11 [2015-05-15]. ISBN 978-0-521-19199-9.
- Syrett, David. The Defeat of the German U-Boats: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Studies in Maritime History.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0. ISBN 978-1-57003-952-2.
- Szpilman, Władysław. The Pianist: The Extraordinary True Story of One Man's Survival in Warsaw, 1939–1945 2nd. Picador. 2002. ISBN 978-0-312-31135-3.
- Taylor, Telford. Sword and Swastika: Generals and Nazis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95. ISBN 978-1-56619-746-5.
- Tooze, Adam.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New York: Penguin. 2006. ISBN 978-0-67003-826-8.
- U.S. War Department. Chapter I: The German Military System. Handbook on German Military Forces, 15 March 1945, Technical Manual TM-E 30-451.. 1945 –通过Hyperwar Foundation.
- Van Creveld, Martin. 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 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2. ISBN 978-0-31309-157-5.
- von Bischofhausen, Otto. The Hostage Case (PDF). Report to Commanding Officer in Serbia, 20 October 1941 Concerning Severe Reprisal Measures.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Nuremberg, Allied-occupied Germany: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1950 [1941]. OCLC 312464743.
- Wette, Wolfram. The Wehrmacht: History, Myth, Real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674-02213-3.
- Wette, Wolfram. Ein Judenratter aus der Wehrmacht. Feldwebel Anton Schmid (1900–1942) (PDF). Müller, Julia (编). Menschen mit Zivilcourage. Mut, Widerstand und verantwortliches Handel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Lucerne: Kanton Luzern. 2014: 74–82 (德语).
- Wheeler-Bennett, John.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London: Macmillan. 1967. ISBN 978-1-4039-1812-3.
- Whitley, M.J. Warship 31: Graf Zeppelin, Part 1.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Ltd. July 1984.
- Wienand, Christiane. Returning Memories: Former Prisoners of War in Divided and Reunited Germany.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2015 [2018-09-22]. ISBN 978-1-57113-904-7.
- Williamson, David G. The Third Reich
 3rd. London: Longman Publishers. 2002. ISBN 978-0-58236-883-5.
3rd. London: Longman Publishers. 2002. ISBN 978-0-58236-883-5. - Zeidler, Manfred. The Strange Allies – Red Army and Reichswehr in the Inter-War Period. Schlögel, Karl (编). Russian-German Speci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losed Chapter?
 . New York: Berg. 2006: 106–111. ISBN 978-1-84520-177-7.
. New York: Berg. 2006: 106–111. ISBN 978-1-84520-177-7. - Zeiler, Thomas W.; DuBois, Daniel M.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John Wiley & Sons. 2012. ISBN 978-1-118-32504-9.
- Zhukov, Georgy. Marshal of Victory, Volume II. Pen and Sword Books Ltd. 1974. ISBN 978-1-78159-291-5.
- Deighton, Len. 《第三帝國閃擊戰:從希特勒的崛起到敦克爾克的陷落》. 星光出版. 1996. ISBN 957-644-249-4.
线上网站
[编辑]- AFP. Germany struggles to stop Nazi war payment suspicions. The Local. 2019-02-28.
- Axelrod, Toby. German Jewish leader urges cancellation of pension payments to former SS members. The Times of Israel. 2019-03-27 [2019-06-12].
- Binkowski, Rafael; Wiegrefe, Klaus. How Waffen SS Veterans Exploited Postwar Politics. Der Spiegel. 2011-10-21.
- Christmann, Rainer M.; Tschentscher, A. BVerfGE 36, 1 – Grundlagenvertrag. servat.unibe.ch. Das Fallrecht. 2018-02-05 [2019-01-17].
- Department of State. RG 84: Switzerland. National Archives. 2016-08-15 [2019-05-16].
- documentArchiv.de (编). Wehrgesetz Vom 21. Mai 1935 [Military Law of 21 May 1935]. Reichsgesetzblatt (Berlin: Reich Ministry of Interior). 2004-02-03, I: 609–614 [1935] [2019-04-06] (德语).
- Gmyz, Cezary. Seksualne niewolnice III Rzeszy [Sex Slaves of the Third Reich]. Wprost. 2007-11-22 [2019-03-11] (波兰语).
- Groeneveld, Josh; Moynihan, Ruqayyah. The German army is still struggl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s Nazi past, according to historians. Business Insider. Business Insider. 2020-04-03 [2020-09-21].
- Hickman, Kennedy. Battle of the Atlantic in World War II. Dotdash Meredith. 2015 [2015-05-20].
- Germans invade Poland. History (American TV network). 2010-03-04 [2015-05-21].
- Knight, Ben. The German military and its troubled traditions. Deutsche Welle. 2017-05-16.
- Le Faucheur, Christelle. Were US POWs Starved to Death in German Camps?. 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2018-07-23 [2019-02-11].
-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Judgement : The Accused Organizations. Avalon.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2008 [2019-01-17].
- Peck, Michael. Exposed: The Secret Ex-Nazi Army That Guarded West Germany.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7-02-04 [2019-01-11].
- Reichsgesetzblatt. Die Verfassungen in Deutschland I, no. 52. 1935 [2018-0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4) (德语).
- Scholz, Kay-Alexander. German army instills new traditions to move away from troubled history. Deutsche Welle. DW News. 2018-03-28 [2019-01-16].
- Timm, Sylvia. Verdienstorden der Bundesrepublik für Historiker Wolfram Wette [Order of Meri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or Historian Wolfram Wette]. Badische Zeitung. 2015-05-04 [2016-12-22] (德语).
- Trueman, Chris N. Blitzkrieg. historylearningsite.co.uk. HistoryLearningSite. 14 May 2015a [2015-05-20].
- Trueman, Chris N. The Battle of Barents Sea. historylearningsite.co.uk. HistoryLearningSite. 18 May 2015b [2015-05-13].
- USHMM. The German Military and the Holocaust.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Holocaust Encyclopedia. n.d. [2019-01-13].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n.d. [2019-09-08].
- Wiegrefe, Klaus. Nazi Veterans Created Illegal Army. Der Spiegel. 2014-05-14 [2019-01-11].
- Wildt, Michael; Jureit, Ulrike; Otte, Birgit. Crimes of the German Wehrmacht (PDF). 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2004 [2008-11-28].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8-12-08).
- Yad Vashem. 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Yad Vashem. The World Holocaust Remembrance Center. n.d. [2019-01-16].
